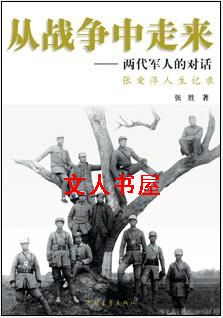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父亲的抗战岁月,一半在淮北;一半在苏北;江淮大地留下了他的足迹。
1 苏北战场
路西一仗,10旅被打惨了。黄克诚从华北带来的这支劲旅——八路军344旅,现在只剩下两个团四个营共3200人了,黄克诚能不心疼吗?他提议,将父亲创建的九旅调归4师,换回曾经调出去的10旅。这个建议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合理的。九旅兵强马壮,又是皖东北土生土长的部队,4师路西失利后,也急需加强。10旅是他自己带过来的,苏北局面相对稳定,过来后可以休养生息。由于路西豫皖苏根据地的丢失,华中局将皖东北改为淮北苏皖边区,成立淮北军区,由邓子恢、刘瑞龙、彭雪枫分别执掌。我父亲被任命为3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率10旅奔赴苏北战场。
命令是陈毅宣布的,他专程来了一趟皖东北。他什么时候都不改他特有的洒脱幽默的作风,在大会上他说,我这次就把你们的旅长带走了,你们有意见没有啊?掌声稀稀落落。人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在部队干过的人都明白,自己追随的首长晋升,是好事,当然应该鼓掌;但部队又要并入一个新的单位,过继给人家,成了后娘养的,有了难处去找谁呢?这掌真鼓不起来。许多地方的新四军纪念馆都保存了父亲离开九旅时的照片,中间是陈毅,还有接管他们的彭雪枫师长,新任九旅旅长的韦国清和九旅的其他领导干部,被欢送的主角我父亲却站在最后排的边角上。这是一张喧宾夺主的照片。好奇怪啊,或许是无意识的,是父亲一贯低调的风格所致?或许是有意的?他想跟他的部队说,我已不再是九旅的灵魂了,但我的心,将永远伴随着你们,牵挂着你们。中国革命任重道远,前方的路充满艰险,走好啊,我的战友,我的兄弟!
或许,什么都不是……
新四军的军部和华中局也设在苏北,3师成为拱卫军部的一支劲旅。在这里,父亲和他敬爱的领导人陈毅元帅,以及在战略思想上支持过他、肯定过他的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以自己的成功赢得了上级对他的信赖和器重,他不再像皖东北时期那样孤军奋斗了。这无疑对他今后的人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年生死两茫茫”。自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丢失,红军主力被迫转移。父亲随中央大队长征北上,陈毅和其他战友粟裕、叶飞、钟期光、傅秋涛等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今天,在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之后,老战友们重逢,大家不仅健在,而且戎装齐整、兵强马壮。还是在上次共同开辟苏北时,正赶上父亲打开皖东北的局面,雄心勃勃;陈老总和粟裕又刚指挥了黄桥决战,各自的胜利使他们沉浸在共同的喜悦之中,抚今追昔,怎不叫人热泪盈眶!陈毅元帅即兴写下了他那著名的诗篇: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悲喜之情,跃于纸上。
父亲说:“陈老总的诗是在大会上写的,黄老(注:黄克诚)拿给我看,我也和诗一首,‘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敌后旧属归。’我是他的部下,就用了旧属;忆昔,过去几次听他的教导;‘南援北进江淮会,兄弟共举红旗飞。’兄弟指的是八路军和新四军,陈从南边,黄从北边,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都这么多年了,父亲谈起和陈老总会师的往事,还是那么真切和兴奋。
父亲要与黄克诚共事了。和认识彭雪枫一样,父亲也是在红3军团和黄克诚相识的,长征中,他们都在彭老总手下,黄是4师政委,父亲是师政治部主任;土城战斗后,红3军团在扎西改编,黄是红10团政委,父亲是红11团政委。
黄克诚生于1902年,比父亲大8岁。也许是他少年老成吧,8岁的跨度,就像两代人一样遥远。父亲习惯称黄克诚为“黄老”,也有时称“黄瞎子”。在父亲当年写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长征中的黄克诚的:“四师的黄政治委员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用那嘶哑的喉音在对团一级的干部们谈话。他握着他那瘦得骨头都看见的手,(他说)‘一颗流弹牺牲了洪师长……捉着蒋介石来坐铁笼!’”(注:张爱萍《第六个夜晚》1936年写于瓦窑堡。收集于1954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父亲回忆,长征进广西,过两河口,红4师师部住苗寨。白崇禧为了离间苗人和红军的关系,经常派人化装去苗寨滋事,搞些小名堂。一天半夜,师部突然起火,黄克诚住的苗家小木楼浓烟滚滚。父亲说他组织营救:“整个屋子浓烟滚滚,黄克诚这个家伙,还在那里磨磨蹭蹭的,我急了,对警卫排长喝道,架起来,拖走!黄还在那找,我的眼镜!我的眼镜!”父亲边说边学,哈哈大笑。
黄克诚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的性格特征与彭雪枫和我父亲不同。从我母亲嘴里我知道,他是个理性人物,处事缜密,深谋远虑;性情温和,但却外柔内刚。外表看起来,他灰色低调,不像彭雪枫,潇洒英武之气溢于言表。当年在苏北3师师部工作的扬帆同志蒙冤下狱时,写了很多诗词,追忆他的领导和战友。其中对黄克诚的描写是:“推食解衣空恋旧,慰海勤勤未敢忘”;而描写我父亲则是:“狂人介士尽云从,年少将军气度宏”。历史不能再现,但从扬帆的诗中不难看到,两个人风格和气质的差异跃于纸上。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黄克诚。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五一、十一的夜晚,党的高级干部是可以带子女上到天安门城楼看放烟花的。在天安门城楼上,黄克诚戴一副眼镜,裹着大衣默默地坐着,不像父亲和陈赓、杨勇、刘亚楼、陈锡联那样相互开着玩笑。
再见到他时,已是“文革”结束后的事情了。黄克诚已经很老了,戴着很深的墨镜,坐在轮椅上。他像一尊雕像,凝重而威严。我和周围的青年军官们不自主地都举起手来,向他致以军礼,虽然我们知道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是他提议把父亲调来给他当副师长的。他是这样谈他自己的:“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注:《黄克诚自述》200页)
应该说,他们之间是一个最佳的组合。黄的老谋深算,我父亲的血气方刚。但我听母亲说:“是不是有别的考虑就不知道了,但黄老和你爸爸之间,不是太和谐的。”
喔,是这样,为什么呢?
“黄偏重于稳健,而你爸则是个拼命三郎。再加上你爸这个人,事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意,又不讲究方法,谁愿意要他!”
我问父亲,谁调你去3师的?
“我怎么知道。”回答的真干脆!
当时黄克诚不仅是3师的师长兼政委,还是苏北根据地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黄在他的回忆中说道,苏北这个地区长期为反动地主武装所把持,土匪、封建会道门遍及各地。他们打砸抗日政府,杀害干部,抢劫群众。更有甚者,刚来苏北,就遇到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黄克诚说,他到了苏北后,着力抓了几项工作:抢修海堤;消除匪患;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加强主力;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统一战线。黄说,邹韬奋、范长江、钱杏(阿英)、沈其震、薛暮桥、贺绿汀等,这些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到来使这块敌后根据地一时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苏北留给我父亲的记忆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父亲是从另一个角度回顾的:“苏北这个地方,在人家眼皮底下,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他说:“如佃湖,滨海县的大、小尖子,陈家港等,都是敌人薄弱的部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扩出去。佃湖就是伸到我们这边的一颗钉子,非常孤立的,完全可以拔掉。我们应该抢在敌人之前,调整态势。”
父亲继续说:“……我提了几次也就算了。后来敌人扫荡就是从佃湖这里开始的,一下子就插到我纵深来了。刘、陈说是右倾,重了。但保守是有的,太过分强调保存实力了。”
我已经感觉出来了,父亲调到3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
难得一闲。军人不打仗还能做什么?从皖东北东征西讨的日子走过来,可真不习惯,但总不能无所事事啊,不如下去搞整军,整顿纪律,组织练兵,提高战斗力。父亲说:“既然这样,不听就算了。我向黄克诚提出,我还是去整顿部队吧,都是游击队起的家,不正规,不训练,怎么能打仗?黄很赞成。我说,先从军容风纪抓起,我们师里领导可要以身作则喔!黄说那没有问题。24团团长谢振华,3军团的保卫干事,就从他的部队开刀。以后他们搞了阅兵式,很是轰轰烈烈。解放后碰到,他还和我说起这段往事。黄克诚军容风纪最差,从来不打绑腿,敞开个领子,揣个手。我就是要将他的军,我说你一个师长军容风纪都不整,要我怎么说服下面?黄克诚这次很痛快,哈,第二天就打起了绑腿。他说,这是他第一次。”
你就不怕他不高兴?我问。父亲说:“怎么可能?他是太了解我了,都计较起这些,还怎么干工作?”他讲起了长征路上的一段往事:
红3军团夺占娄山关占领遵义后,国民党吴奇伟的两个师反扑上来,首先对防守在老鸦山左翼的我父亲指挥的红11团发起攻击。父亲说:“敌人从一个团增加到两个团,我们三个营都顶上来了,胶着在那里,但后续的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我看光靠自己是不行了。黄克诚的10团守在老鸦山顶上,我跑上去要他配合从敌人侧面出击一下。黄不干,说他的任务就是守卫老鸦山顶。我看说服不了他,只好又跑了回来。想不到的是,敌人看攻不动我们,就改变转向攻击老鸦山顶,10团顶不住退了下来。彭老总命令我们从左侧攻上去夺回主峰,攻了两次没拿下来。这时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彭要我们配合再攻,又把彭雪枫的13团用上,并要他统领12团,他们从侧面,我们从正面,把敌人打下去了。我们一直追到鸭溪,1军团追到刀把水,敌人把浮桥截断,结果后面一个营当了俘虏,吴奇伟的两个师就这样被消灭掉了。”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父亲继续说:“我军大获全胜。军团在鸭溪开战评会,我说,你黄克诚就是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彭德怀很恼火,把黄、张给撤了,黄下连队,张宗逊当伙夫。不久,他们又回来了,有意思。我觉得黄克诚、张宗逊的战术思想不对头,依照我的打法不会损失那样大。我同黄、张相处的是很好的,打仗总有胜败,但这次黄是太固执了。”
对这一战斗的回述,黄克诚和父亲两人是有差异的。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团长张宗逊已带队出击了,我怎么好擅自离开阵地。另外,他回忆,林彪对他讲,敌人其实已经撑不住了。我理解黄的意思是,形势未必有那么严峻。我没有对这个战例做过详尽的考察,其实孰是孰非并不重要,也许是年代久远,记忆有所偏差;也许是两人观察问题的切入点就不一样。我只是想要证明前面我父亲和黄克诚在作战问题上是有过分歧的,他们可以在彭老总面前开诚布公地争吵,但并不因此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一直把黄作为兄长,尊重他、维护他,黄也把他视如小弟,一直器重他、关心他。
我说父亲,就你这样,哪个领导会喜欢你?
父亲说:“干什么要别人喜欢?我这个人干起事情来,有时候是有些左倾、鲁莽,只想要干好,不讲究方式方法。打土城时,同敌人对峙在那里,部队很疲劳,在阵地上打起瞌睡来。我在4师当政治部主任,召集各团开会,在会上批评杨勇,说你们10团在阵地上表现最差,打瞌睡。有的同志提醒我,说杨勇同志都负伤了,我说,负伤也不光荣。话一出口,心里很后悔……”
这件事,他曾提过多次,因为自己的情绪一时失控,使战友受到委屈,当时的那种内疚之情,60年都过去了,可见自责之深。
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历史。如果说黄克诚像是个兄长,他对这个年轻气盛的小兄弟恐怕真是哭笑不得了。
1942年11月7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军部和3师原计划组织阅兵式,然后是运动会;晚上还有演出,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