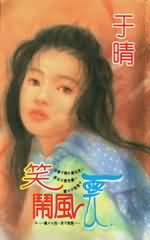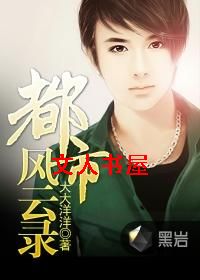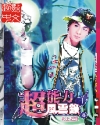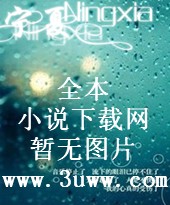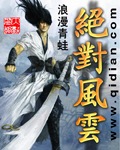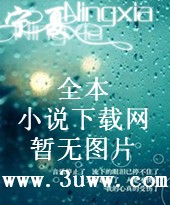永乐风云-第1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过事情的发展大大超乎解缙所料。登基未久,永乐便颁布诏旨,在左顺门旁的文渊阁设置内阁,陆续简拔黄淮、胡广、杨荣、解缙、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入阁参预机要政务,并各有擢升。(胡靖之“靖”为建文所赐,永乐登基后恢复本名胡广;杨荣本名杨子荣,永乐为其更为现名)这七人皆是才华出众的翰林词臣,其中解缙排名第四,被授予正六品侍读之位。三个月后,永乐再次下旨,解缙晋侍读学士、从五品,位居内阁之首!
短短四个月,解缙从一个从九品待诏连升八级,一跃成为从五品的侍读学士,其擢升之快,在归附的建文旧臣中首屈一指。而且,侍读学士是翰林院之职。按制,翰林院以学士最尊,其下依次是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眼下学士和侍讲学士二职皆空缺,解缙便以侍读学士身份充任翰林院掌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士林领袖!
突如其来的擢升,饶是解缙阅尽沧桑,一时也有些懵懂。待回过味儿来后,他顿时被巨大的喜悦和兴奋所笼罩。连升八级,执掌翰林,这固是一大喜事,但更让解缙动心的,却是内阁这个新鲜的物事。内阁乃永乐首创、不但洪武朝,就是历朝历代也从未有过这个衙门。按照永乐的谕旨,内阁阁臣职在参预机要,也就是辅佐皇帝处理国政,这可是宰相的职权!虽然皇帝的意思也很明白,阁臣只是顾问,并无决策之权,但一想到能够协助皇帝作出决策,进而对天下大政产生影响,解缙仍激动得几乎不能自持。
解缙十九岁入仕,年纪轻轻便被太祖视为天下奇才,其才具绝非寻常官宦可比,“经济天下”正是其一生抱负所在。只是一朝成名之后,解缙却长期郁郁不得志,十几年宦海沉浮,到头来只混了个九品末官。残酷的现实,一度让解缙伤心乃至绝望。可是如今一切都不同了。新的永乐天子赏识自己的才华,并委以辅政重任,这犹如一片甘霖,落到解缙几近枯涸的心田里,让他重新热血沸腾。解缙感谢永乐的器重,他暗自下定决心,要用自己全部的才华和忠诚报答永乐,辅佐这位皇帝开创一个千古未有的富强盛世,让他和自己都名垂青史,为万世景仰!
“喔喔喔……”,就在解缙心潮澎湃的当口,窗外隐隐传来公鸡叫鸣之声。解缙伸了个懒腰,慢慢从床上爬了起来。一名婢女早已在门外候着,听得屋内声响,忙轻轻推门而入。
热水洗脸,青盐拭牙,一切都如往常。待盥洗毕,解缙来到花厅,草草进了早膳,然后穿上绣着小杂花纹的青色盘领右衽公服袍子,随即精神抖擞的出门而去。
早朝于辰时在华盖殿举行。通常,此类常朝所奏都是已议定好的四方之事,并无甚紧要之处,解缙作为内阁之首,对内容已事先知晓,故不必太过关注,只需循规蹈矩旁听便可。散朝后,百官各自回衙门署事。解缙和同为阁臣的侍读黄淮却故意放慢脚步。未多时,乾清宫打卯牌子马云便小步跑过来道:“两位学士请留步,皇爷召你们到乾清宫见驾!”
自设立内阁以来,七位阁臣经常随驾侍候,其中又以解缙和黄淮二人最受器重,几乎每日都会被永乐唤到身边问事,两人对此也都习惯了。听马云传旨,解缙与黄淮对视一眼,只道声“遵旨”,也不再多说,遂跟着马云向后宫走去。
二人刚跨进乾清宫御书房的门槛,永乐便面带微笑地坐在案后向二人招手道:“不必行礼了。朕于一事颇为不解,召尔二人前来解说!”
“阿!”解缙、黄淮二人忙一躬身,一阵小碎步走到近前。
永乐拿着一本发黄的书,指着其中一页道:“朕读这《水经注》,其中《江水篇》记着:‘江水又东,迳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峡中有瞿塘、黄龛二滩。’可朕记得,瞿塘乃峡名,是三峡中之首峡,此广溪峡何来?尔等可知?”
永乐说完,解缙与黄淮皆是一愣。《水经注》虽不是经史,但也是地理之学的集大成之著,以解、黄二人之博学,早已是读得滚瓜烂熟,可永乐一问起,二人却是怎么也记不起来。过了半天,黄淮方嗫嚅答道:“回陛下,臣等不才,却不知《水经注》中竟有此节?”
“哦?”永乐有些奇怪地应了一声,随即把手中之书递与二人道,“书中写得明明白白,尔等可是记错了?”
黄淮把书小心接过,解缙忙凑过头来。待读完永乐所指之章,黄淮仍是稀里糊涂,解缙却似心有所动。他从黄淮手中把书拿过,又仔细翻看一遍,眼中突然冒出喜悦的光芒。他捧着书,欣喜地对永乐奏道:“陛下,这《水经注》似是北宋绝本,陛下从哪儿找到的?”
“哦?”朱棣有些意外道,“前些日宫里人清理文楼,从旧书堆里扒出来的。近年苏松一带水患频繁,户部尚书夏元吉奉旨治水,至今尚无佳音,朕每思之,心中颇为忧虑,便找了此书出来,看看关于河道的记述中有无可鉴之处。尔怎知此乃绝本?”
解缙小心地将书摊开递到永乐手中,然后指着其中书页道:“陛下请看,此书乃雕版所刻,从版式看,用的是四周单栏。此种版式唯在宋初行过一阵,后多用左右双栏或四周双栏。宋初距今近四百载,所流传已不多;而靖康之祸后,中原涂炭,金人北狄出身,毁我华夏文物无数,此类雕版由是愈发稀有。且宋以后,《水经注》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臣所读便有好几版,但从未记过广溪峡一段。故臣敢说,此十有八九便是北宋绝本,即便当今世上仍有幸存,其数也必十分稀少!”说到这里,解缙又一躬身,恭恭敬敬地道:“此书成于宋初,应未经后人矫改,极有可能便是郦道元之原著。陛下竟能于不经意间寻得此等珍稀,实乃郦学之幸也!此书再现,于地理之学大有裨益!此全赖陛下慧眼独具之功!”解缙借着讲解此书来历,一边展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学,一边又好好拍了下永乐的马屁。
解缙这马屁拍的正好,永乐龙颜大悦,当即大笑道:“果然是学通古今,连刻板都知晓得一清二楚!当今天下第一才子,朕看非尔解大绅莫属!”
“陛下谬赞,臣岂敢当此殊荣?”得到永乐这么大的夸奖,解缙心里当即乐开了花。不过他肚子里的货还不止这些。谦逊过后,解缙又信心十足地道:“陛下刚才所说广溪峡,臣也想起来了!”
“哦?”永乐用欣赏地目光瞧着解缙道,“你可知其来历?”
“是!”解缙神采飞扬地答道,“臣读唐诗,曾阅得杨炯曾于武则天天授元年作有《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三首。其中《广溪峡》一首开头为:‘广溪三峡首,旷望兼川陆。山路绕羊肠,江城镇鱼腹……’;而到肃宗朝时,诗圣杜甫又作《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一首,于此处首次见瞿塘峡之名。既然广溪峡为三峡之首,那出白帝城,自应进广溪峡,而杜甫却题放船出瞿塘峡。由此推之,瞿塘峡应就是广溪峡。而以瞿塘峡之名所以流传于世,或是杜甫之名太盛,后人因其诗之故,反而以瞿塘名峡,而广溪峡之名倒是无存了!不过杜甫从何处得‘瞿塘’之名,却是无考!”
解缙说完,不光是永乐,连一旁的黄淮也是不得不由衷佩服。一样的翰林词臣、内阁同仁,解缙博闻强记,皇帝随便一问,他便能引经据典,侃侃道来;而反观他黄淮自己,却只能瞠目结舌,一句也插不上口。自愧弗如之下,黄淮心里多少也有些酸溜溜的。
“解爱卿今日之言,着实让朕开了眼界。”永乐却无暇关注黄淮之感受,只自顾自地感叹道,“朕素以好读书自诩。然经今日一事,方知自己竟是井底之蛙!”
“陛下过谦了!”解缙忙答道,“《水经注》不过是杂学,诗词更是雕虫小技。陛下乃大明天子,自当以经史为重,此类旁门左道,不学亦无不可!”解缙这话,一半是为永乐开解,一半倒也是发自内心。虽然解缙本人是什么书都读,但就其本心,他从来都是以经史为重。在这位有着胸怀天下的大才子眼中,只有经史,才是一展抱负的根本;至于诗词等技,解缙虽然精通,但从没把他们当过正学。正因为如此,解缙认为永乐不通杂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永乐笑笑,又扫视手中的宋版《水经注》一眼,忽然心中想起一件事来……
上个月的初六是太祖高皇帝的忌辰。这一日,永乐遵礼部议定之礼,先着淡浅色衣至奉先殿祭祀,后又率文武百官亲诣孝陵致祭。待从钟山上下来,永乐命朝臣各自回衙署事,只携太子少师姚广孝一道进宫。待回乾清宫后,二人到御书房坐下,永乐挥手屏退下人,一本正经地望着姚广孝道:“少师,朕近来心绪杂乱,有诸多烦闷事,却不知何以开解,还望您不吝赐教!”
姚广孝正在啜茶,闻言遂将茶杯放下,呵呵道:“陛下素以孝悌闻名天下,此值高皇帝忌辰,故心有不宁,这也是人之常情!”
“此自不假!”永乐知姚广孝奉承,只浅浅一笑,旋敛了又道,“然并非全部。朕之所以烦闷,实为心中迷惑。”说到这里,永乐端正了坐姿,认真地道:“朕登基已近一载,期间虽不能说是旰食宵衣,但自认为也称得上勤勉。然回首这一岁中作为,朕所做者无非是稳定朝纲、恢复民生等临时之举,虽然必要,但均非长久之策。如今时过境迁,国家已百废初兴,接下来大明的路该怎么走,朕却始终没有个定见。今日在皇陵享殿对皇考画像叩首时,朕心中实为不安,寻思若不能打理好这大明天下,将来九泉之下恐无颜面见皇考!念及于此,朕愈发觉得应有所打算。正所谓纲举方能目张,今大明当以何略为纲,还请师傅教朕!”
永乐娓娓道来,姚广孝一直默然静听。待他述毕,广孝仍迟迟不语,良久方眼光一闪,不无挪揄地道:“陛下何以有此虑?当初奉天靖难,便是为着恢复洪武祖制!既有言在先,萧规曹随便就是了!”
永乐脸一红,自失一笑道:“自是以洪武祖制为准!然祖制虽佳,亦有不尽详备之处,若能在其上有所增益,使之更加有利于国家,也是善莫大焉!何况朕身为继任,自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太祖基业发扬光大!若仅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那未免太过庸碌,绝非贤君之道,太祖在天之灵亦未必欢喜!不知师傅以为然否?”
姚广孝会心一笑。尽管永乐话语间遮遮掩掩,但道衍却立刻就明白了内中的深意,并由此看穿了永乐的心机。
姚广孝追随永乐二十年,早已将这位皇帝的内心揣摩得淋漓尽致。在他眼中,永乐虽然城府颇深,但究其实却是个心气极高、志向极远、欲望极强之人。当燕王时,他便是亲藩中的翘楚,功业远超其他兄弟;如今做了皇帝,他自然也不甘为一平庸之主,而必要有一番作为。尽管永乐口口声声说遵从洪武祖制,但广孝清楚,以休养生息为宗旨的太祖朝旧制,根本无法满足永乐的欲望,无法满足他的雄心!只有奋发有为,建立不世伟业,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渴望和追究。何况广孝还知道,永乐这个皇位终究来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若无所作为了此一世,将来少不了被人腹诽,留下个“篡位”的难听骂名。要想改变这种结果,唯一的办法就是效法逼父弑兄的唐太宗,做一个大有为之君,打造一个冠绝古今,足以为万世楷模的辉煌盛世,如此方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与民生息就能做到的。
当然,永乐绝不能否定洪武祖制,至少表面上不能。这不仅是因为祖制乃太祖高皇帝所定,照章遵行乃孝子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当初永乐就是以建文悖离祖制为名起兵靖难,进而夺下这万里河山。否定洪武祖制,就是抽自己的嘴巴,就是摆明了告诉天下人:所谓奉天靖难实乃欲盖弥彰,他永乐内心所觊觎的,一直都是这顶金光闪闪的皇帝冕冠!
但表面上不能,并不代表内心不想。洪武祖制已成为横在永乐面前的一大阻碍。要想有所作为,要想缔造永乐盛世,就必须开拓进取,就必须突破洪武祖制的限制。尽管永乐口口声声只要什么“有所增益”,但姚广孝已经明白,永乐其实是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在他看来已不合时宜的洪武祖制,改变这个已在大明推行了三十年的国政大纲。眼下他所为难的,只是废除旧制后如何举措方能实现心中理想,以及如何使这改制之举不给人留下话柄这两条而已。这,就是永乐今天召他进宫的真实用意!
姚广孝陷入沉思。自永乐朝建立以来,他便逐渐淡出了权力的核心。这一来是他自觉功成名就,二来也是他年事已高,不愿再为俗事羁縻。但姚广孝毕竟是实际上的靖难头号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