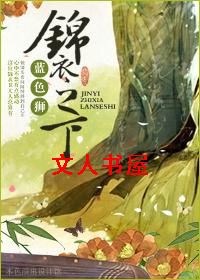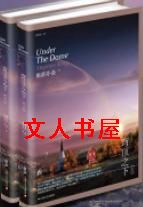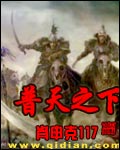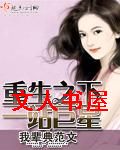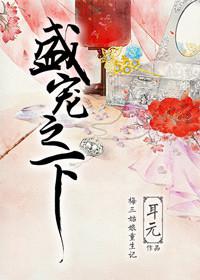普天之下-第1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然给商人们免税,官府看似亏了一些,但是百姓得到救济,这是个善政。大大的善政。”耶律楚材捋着胡须赞赏道。
“大人这么说。我家国主一定很高兴。不过嘛,我家国主却很不乐观啊。当初我家国主曾在拖雷殿下允诺采买赋税,三年以后,一次**纳银锭二十万两,粮二十万石,帛二十万匹,这是个相当不小的数目啊!”王敬诚面露色地解释道,“且这次商人们送来的粮食毕竟有限,明春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所谓采买,也就是承包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赵诚不得以而为之的办法。
“这么多?”耶律楚材大吃了一惊,旋即晒笑道,“不儿罕总是有办法,我想他既然这么说,那就一定能办到。”
“耶律大人你也这么想?”王敬诚脸上挂着很不屑的表情,却是半真半假,“赋税采买不过是权宜之计,要不然蒙古的老爷们若是要西夏百姓交税,这如何是好?我华夏神州,何时有过天下赋税采买之制?”
耶律楚材默然。
“不儿罕身在何处?”耶律楚材又问道。
“我家国主这两天身体有些不适,不便见客,耶律大人不妨随在下入城,在下先安排大人住下,然后再请我家国主拜见大人!”王敬诚道。
“他身体不适?”耶律楚材大吃了一惊,“不儿罕一向身康体健,几日不纵马狂奔就觉得不自在,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倒了呢?从之,你们身为他的属下,应该多担待一些政务才是啊。”
耶律楚材以为赵诚是因为太忙了而病倒地,实际上是赵诚将窝阔台与拖雷送走之后,就将自己关在自己的卧房里不见任何人。
“大人教训的是!”王敬诚虚心地说道。
入得城来,只见城墙之下又围着几堆人,个个都伸着脖子看着贴在墙上的告示。
“那是做什么?”耶律楚材问道。“哦,这是安民告示。”王敬诚解释道,“大战之后,百废待兴。官府手中得来的粮食,又不可浪费,凡是有一技在身者,尽数录用,有所付出必有所得,我们不养闲人,也没有粮食养闲人。铁工院召铁匠打制铁器,木工院制木器,以待明年播种之所需之铁木农具,织工可以将收上来的毛纺纱、织毯、织布,转卖给商人们换来粮食,精壮一部分抽出来趁着下雪前开挖水渠,疏通水道,另一部分入贺兰山打猎。夏国素来地少缺粮,但从不缺精盐,盐州乌、白二池所产青白盐,天下闻名,当年夏宋交恶,宋国朝廷屡屡禁盐却几无可禁,概青白盐质优价廉也!故我家国主已命人采盐,输往中原或者他地,以获其利。”
“若是文士,那又该如何呢?”耶律楚材饶有兴趣地问道。
“这也好办啊,城内城外有不少孩童,因战乱饥荒或疫病,家中无人可投靠,生无所倚,国主心存砂忍,命我等开义学,命刘翼刘明远全权主持,让西夏文士们充当教席。还有一些文士在译馆里将蕃文书籍译成汉文,每日都会得到粮食。”王敬诚笑着道,“将来,国主还有意要为夏国修史,这些夏国文进士当然不会闲着。”
“不儿罕实在是贤臣呐!”耶律楚材抚掌大喜道,“开源以筹粮,节流以赈灾,又不会让百姓无所事事而滋生祸事,安定民心,百工皆有所养,此治乱之道也。难得的是,在这乱世之中,文士也能得到照顾,就是中原也不及如此啊。”
“我等其实还是很惭愧的。中兴府、灵州还好说,河西沙、瓜、肃、甘、凉五郡也还算不错,真正难地是那些偏远之地,鞭长莫及也,官府手中即是有粮,也受困于路程险阻,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那些蕃人聚居之地,民风剽悍喜好斗勇,又受制于族言,难以深入。”王敬诚道。
“不儿罕体恤百姓,乃仁臣也,贤臣也,国士也!”耶律楚材称赞道,“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百姓有福了。”
安顿好了耶律楚材,王敬诚连忙来探望赵诚,只见赵诚卧房的外面刘翼和徐不放两人来回踱着步子,百无聊赖无可奈何。
“咱们这位国主,跟一般人可不一样。你可以当面指摘他的不是,也可以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但若是拿家室来威胁于他,可谓是触了逆鳞!”刘翼苦笑道。
然而刘翼话音未落,已经将自己关在卧房内一天两夜的赵诚打开了房门,当他满脸憔悴地走出来时,刘翼等人大感意外。王敬诚等人正要再劝赵诚几句,赵诚却摆了摆手,径自细致地刮着胡子。
他对着一面从皇宫中搬来的铜镜,极为细致地用一把锋利的剃刀耐心地刮着,好似生怕将自己地脸刮破,然后又洗了一个热火澡,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将身上一切颓废之气一扫而空,如同换了一个人。
“从今天起,我算是洗心革面了!”焕然一新的赵诚对着心腹们说道。
第二十章 长缨在手(完)
赵诚陪着耶律楚材去新设的所谓译馆里视察。
这个译馆设在原西夏皇帝与群臣议事的政事堂里,斯人已去,徒留空荡荡的殿宇。殿中的正中,一溜摆着数排桌椅,四周摆放着赵诚四处搜罗来的成堆文籍以及笔墨纸砚,还有数位小厮伺候着,数十位身着长衫的文人模样的人正在工作着。
“贺兰国王驾到!”有把守的兵士高声呼道。正在忙碌的文士们闻言连忙起身,正在想如何行礼才合适或者还是不行礼,赵诚却一马到先进得殿堂,摆了摆手,示意大家继续。赵诚扫视了一眼,只见那位高智耀赫然在列,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大人请看,西夏地处中原西北,看似蛮荒之地,然而却并非不知文也。中原人称北方异族为胡,南方为夷,西方为蕃或羌,然而党项人却不认为蕃字是个不雅之字,他们也常自称为蕃国、蕃人,口中所说的也是蕃语,所写的也是蕃字。”赵诚捡起一本书指着扉页道,“这是党项人编的《蕃汉合时掌中宝》,主旨就是为了蕃人学汉文汉人学蕃文,著者开篇就明言:不学蕃言,岂和蕃人之众;不会汉语,岂入汉人之数。蕃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蕃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耶律大人,此著者所言乃至理名言是也!”
“国主看似对夏人很是推崇?”耶律楚材疑惑道。
“非也。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赵诚回答得很简短。
“国主心胸广大,耶律不及也!”耶律楚材道,“不过,天下之大,族群归属之数不知多少,夏人素民风剽悍,乃慷慨斗勇之辈,又兼有言语习俗之不同。国主将来如何面对?”
“呵呵!”赵诚故意将耶律楚材从头至脚打量了一番,这让耶律楚材很不爽。以为赵诚又想拿自己开玩笑。
赵诚见耶律楚材有些不高兴,便开口说道:“我刚才说中原汉人称北方异族为胡人,耶律大人好像并无任何不悦之色。”
耶律楚材心中一怔,倒吸了一口凉气,惊讶地说道:“你真够歹毒地,然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你的想法若要施行起来。恐怕不是三五年就能行得通的吧?”
赵诚只是一提醒,耶律楚材就明白了,因为他是契丹人,而且除了姓氏他的身上看不出一丝所谓胡人的特点,就连身体内的血液早就是汉人成份占了大部分。赵诚的计划就是要同化所有的蕃人,这当然是一个极为宏大的计划,十年二十年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成效。
“史书上说,党项人乃汉朝时西羌之别种,他们原本在河湟及其以西河谷、草原与高地之间放牧、狩猎,中唐时吐蕃人强盛。他们不得不内迁,唐末曾两次被赐姓为李,其首领曾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银、静、绥、宥五州,党项人由此强大。宋初时,又被赐姓赵。赵德明(或李德明)心慕中原文华,曾对儿子赵元昊说他本人三十年来衣锦绮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而赵元昊是个文武双全之人,智谋过人,他想脱离大宋国自成一朝,常言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所以为了称帝,他改姓嵬名,并命人自创一族文字。”
“我契丹人也曾创一家文字,至今识契丹字之人不多矣!”耶律楚材感叹道。他本人就是一个生动地例子,还好他在西域时曾学过一段时间。时移事易,耶律楚材从没想到他学契丹文还要跑到万里之外的西域学习。
“正是如此,党项人创蕃文,元昊坚持给族人剃发,并命汉人戴头巾着汉服,以区分族属。然而党项人本无剃发之习俗,概因元昊自称乃北魏之鲜卑后裔也,抬高自己称帝地本钱罢了。至今,我等所见,蕃文典籍虽多,然多不过汉文,蕃文也大多自汉文译转而成,元昊时译《尔雅》、《孝经》、《四言杂字》,毅宗时上表求宋皇赐御制诗章隶书石本,又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改行汉礼,用汉家之冠服;仁宗时国内多设学舍,崇儒敬佛。百姓当中蕃汉杂居,事农事之蕃人不知多少,只有偏远之地的蕃人才穿皮衣事畜牧,然汉风势不可挡。”赵诚笑着道。
“若是我蒙古大汗将来也兴汉学立科举,则大事可成也!”耶律楚材道。
“呵呵,这要赖大人进言了。”赵诚笑着道,其实很不以为然,“不过,大人不要忘了,我贺兰与中原不同,这里蕃人虽是第一大族,然汉人之数排行第二,元昊立国至今近二百年,儒学通行又有数百年,通晓蕃汉两种文字之文士有不知有多少,施政又少不了汉人,出身汉人的重臣也不知有多少,同职之臣以蕃、汉、降汉、西蕃(指吐蕃)、回鹘为等级之序,民间蕃汉杂居,其俗渐染。如此,施行起来倒也不是难事。”
耶律楚材不置可否,在他看来施汉法是天经地义之事,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难他越是有劲头。赵诚在心里为耶律楚材默哀。铁木真对城市无比的憎恶,他的儿子们也是如此,心腹们也都想着将农田变为牧场,将农夫变成奴仆。
“大人还不要忘了,若是兴科举,那么考中之人是蒙古人多,还是汉人为多?”赵诚干脆抛出这个问题,让耶律楚材思考了大半天。
耶律楚材在中兴府内停留了三天,便要起程赴燕京。他取道贺兰山,从黄河北岸经草原去燕京赴任。
贺兰山下,耶律楚材有些惆怅之感,秋意越来越重了,层林尽染,山抹微云,衰草连连到天涯。北国地秋天太过短暂,最后一批南飞雁从碧空中一晃而过,徒留几分忧愁之感。
“当年撒马儿干一边。你我一别三年,这一次分别。再见时不知又是何夕何年。”耶律楚材骑在马上感叹道。
“大人这般儿女之态让我难以明了,有诗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耶律大人若是赶赴燕京任职,那也是荣归故里,我想天下士子必对大人翘首以待也,大人何必如此消沉呐。”赵诚取笑道。“我想蒙古若是召开忽邻勒台大会,你我又可相见吧?”
“只可惜,大汗生前虽对我另眼相看,但对文士从来就没重视过,河北有不少的文士沦为皂隶,让我心中不安。中原治理,仍是如蒙古草原一般,千户、百户兵民一致也,掌军者又兼管民政,集大权于一身。妄杀滥捕,而府库中却无一尺布帛一石粮粟。”耶律楚材道,“这不是治国之道,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等窝阔台殿下成了大汗,耶律大人不就得偿所愿了吗?”赵诚口中劝道,心中却很不以为然。
“知难而上罢了。”耶律楚材道,“那些蒙古权贵各占土地。私蓄人口为奴,国家却无所得。归降汉军首领,如刘黑马父子史天泽父子之辈又都是地主豪强,难也!”
“耶律大人之主张,在下也极为赞成。只是在下以为。任何主张既便是浅显之道。若是侵占了权贵之人地一亩三分地,施行起来要难上加难。蒙古权贵们自不必说。草原上本来就是分封制,裂土分民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人口也是财富,大人请不要忘了,那些汉军首领都指望着你能施汉法呢,你若是连他们也得罪了,恐怕就于你不利了。”赵诚道,“在下很想知道,耶律大人与王荆公比一比,谁高谁下。”
“集军民两权于一身,独断专行,民怨载道,将对国家不利,我定当规劝将来的大汗,军民分政,各管职事。并立课税,统税权,让国库岁有所得。”耶律楚材道。他对自己的主张确信不疑,并且对未来的治国之路抱着很大的期望。
耶律楚材又问道,“我听王从之说,窝阔台殿下将你的家眷接往蒙古大斡耳朵?”
“确有此事。”赵诚将头扭向一边。
“国主也不必如此念念不忘,所谓质子,古就有之,在蒙古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昔年,耶律留哥归附成吉思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