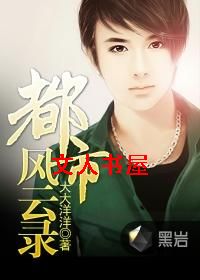将门风云(楚河汉界)-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油娃子不急不躁地翘起拇指试着镰刀的刀口,不软不硬地回了我一句,能哩,窦娥喊声冤,六月天里还落了一场大雪呢。
我就哑住了,拎着镰刀下到田里。
稻子熟了,熟得没了鲜活气,个个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等待着被放倒,被收割。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突然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杀戮的冲动。我岔开双腿稳稳地站在田间,把住六根垄,搂起枯黄的毫无生气的稻谷,挥舞镰刀刷刷刷、刷刷刷地一路向前割去。稻子呻吟着在我的身后成片地倒了下去。割到地头,回头望着那些横七竖八倒伏在地里的稻子的尸体,嗅着刀口和无数断茬散发在空气中的血腥味道,就觉得无尽的感慨在心中涌动起来。
成熟了,我想,妈的是该为成熟欢呼呢,还是该为成熟祭奠呢?
真的下雪了。雪像潮头般从天边滚落下来,只一瞬间,便白茫茫地没了天地。油娃子突然从雪中站起来,满头满脸的冰霜,连睫毛上都挂着白。我问油娃子怎么一会儿工夫就弄成这副模样了?油娃子不搭话,用陌生的眼光望着我,望得我心里直发毛。我走上前定睛一看,这哪里是油娃子呀,原来是个面孔有些熟悉的年轻士兵。奇怪的是,他手里竟然拎着油娃子那半杆汉阳造。
你是谁?我问
我是油娃子。他答道。
浑扯,你不是油娃子。
我是油娃子。
我贴近他的脸仔细看了看说,有点面熟,但你绝对不是油娃子。
他就笑了,说汉娃子,你眼大漏神哩。
我一惊,听这话倒像是油娃子,但看模样又不是。你到底是谁?我又问。
他不再理我,把目光挪向了远处。
我顺着他的目光向远处望去,就看见远处的风雪中有一处山崖。
顶风,好不容易才走到山崖上,脑袋被冷硬的风吹得生疼生疼的。站在崖边向四处张望,总觉得这地方有点眼熟。直到看到远处的电线杆子才反应过来,这不是黑山口那两个兵出事的地点吗?没错,他们就是从这个崖边掉下去的。我恍然大悟地对那个年轻士兵说,怪不得我见你面熟呢,你就是那个班长,那个为救鲁生牺牲了的朱志强吧?
不,他语气坚决地说,我是油娃子。
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油娃子,忍不住生气地质问道,你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嘛,你是谁就是谁,不要冒充别人。你总不至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吧?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他反问道,难道你就真的知道自己是谁吗?一丝淡淡的微笑从他的脸上掠过,他说,其实你也不知道!
真的,我是谁呢?
头疼,疼得像要胀裂了一样。只觉得眼珠朝外暴凸起来,太阳穴憋得嘣嘣直跳,大概如来佛念紧箍咒时,孙悟空就是这么个疼法吧。
我是谁呢?我忍着头疼昏昏沉沉地想,我肯定不是油娃子,但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周汉,不能肯定我是不是黄振中,更不能肯定我是不是李冶夫。
可我真的就不是油娃子吗?
黄振中挥舞着大片刀向我砍过来。嘴里念念有词:周汉,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典型代表!当年罗瑞卿搞大比武时你就是急先锋,罗瑞卿受批判后你虽然有所收敛,但一直是口服心不服,遇到点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邓小平一刮右倾翻案风,你立刻就借口“军队要整顿”在部队大抓军事训练,大搞军事第一,大搞单纯军事观点!
我赶紧抵挡他的刀,只听得“当”的一声脆响,两把刀顶住了,刀刃和刀刃紧紧地咬在一起,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黄振中这一次来势格外凶猛,我眼看就招架不住了,心里的气一阵一阵地往上顶,我忍不住大声叫道,黄振中,你有种就把我的心挖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红是黑!
黄振中一脸正气地答道,不用看我就知道是黑的,是被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染黑的!
我说,黄振中你这是残害忠良哩!我真想挖出你的心看看,看你那个腔子里装的是不是驴粪蛋!
黄振中冷笑道,我这是为革命除害!我告诉你,只要你破坏突出政治,搞单纯军事观点,我黄振中就不会放过你!
我终于被黄振中逼到了坑里,眼看着土一锹锹地扬进来,没过了我的脚,又没过了我的小腿。不行,这样下去我不是白白送命了吗?我突然拼命大喊起来,于恩华!于恩华!你他妈的跑哪去了?
远远地传来于恩华的声音,于恩华说,我在北京呢,我到解放军总医院会诊来了。我现在住在李冶夫家,老政委夫妇俩非留我多住几天呢。
土快埋到腰了,我憋得说不出话,心里却明镜似的,心想这娘们儿不能要了,关键时刻跑北京给自己会诊去了?她哪有什么病?妈的也不知道她能不能长个心眼儿把我的情况跟李冶夫说一说。李冶夫如果肯出面的话,倒真能救下我这条命,就看他肯不肯了。对李冶夫的心思我可是一点也摸不准,我从来都搞不清他到底是对我更信任呢,还是对黄振中更信任。一般情况下,他似乎更看重黄振中,但每到关键时刻,又好像对我袒护得多一些。我很想对于恩华交待点什么,但还没等说出来,就觉得土“呼”地一下填到了脖根儿,脑壳子一阵剧痛,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4
风雪终于停了,太阳突然就把那张大脸贴到近前,脑壳像冻梨似的逐渐缓了过来,一点一点清亮起来了。
有个声音在旁边说:“看,血压降下来了。”
另一个声音说:“严密观察,一定要注意控制血压。如果再复发脑出血,就很难抢救过来了。”
“主任,你看我爸爸还有清醒的可能吗?”这是川川的声音。
“可能性不大,第二次出血加重了脑损伤,恢复意识恐怕很难了。”
“那……我爸爸不就成了植物人了吗?”川川嘤嘤地哭了起来。
小京的声音:“别哭了川川。两次出血相距这么近,能保住爸爸这条命就算不错了。只要爸爸这口气还在就行,植物人就植物人吧。”
植物人?谁他妈的说我是植物人?!笑话,我周汉能变成植物人?!我得起来,我得让他们看看我周汉还是一条堂堂的汉子!我拼命挣扎着想起来,但手脚却像被捆住了似的怎么也动弹不得。
正急着,就听见有人说:“主任,你看病人躁动得很厉害。”
主任可能是在观察,过了一会儿才说:“用点镇静药,防止血压再升上去。”
一针下去,没过多久我就觉得浑身发软,仿佛腾云驾雾般升腾起来了……
螺旋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涂着迷彩的直升机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李冶夫望着下面渐渐远了的部队突然问我,周汉,你和黄振中搭班子时间不短了吧?
是不短了,我恶狠狠地说,我都大便干燥了!
见李冶夫不解地望着我,我就解释给他听,我说我现在被黄振中别得满肚子都是弯弯肠子,能不大便干燥?
李冶夫就乐了,说周汉呐周汉,就冲你这句话,你那根肠子就没多少弯弯。我看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喽!
我说既然知道,你就别拿黄振中别我了。趁早饶了我,想办法把我俩调开算了。
李冶夫说那可不行,没有相克哪能相生呢?他很有内容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当我光拿黄振中别你吗?
我说哼,光别我还不够吗?
不够,李冶夫说,我还指望你给我别他呢。
我?别他?
是啊,这些年多亏你别着他了。李冶夫拍着我的肩膀说,我还得谢谢你呢。
我一下子愣了,傻傻地看着李冶夫。我知道如果我俩不是搭上亲家的话,这种话他永远都不会对我说的。
李冶夫总能让我吃惊,尤其是面对黄振中。
我和黄振中虽然都是李冶夫一手提拔起来的,但我一直认为李冶夫对黄振中更欣赏,更信任。连黄振中自己都说,下级最难得的就是能碰上一个对你信任的领导,我黄振中能干到今天这个份上,每一步都离不开李政委对我的信任、关心和帮助!我这辈子服气的人不多,但对李冶夫政委,我服!
部队搞政治挂帅那会儿黄振中最隆兴,干得可冲了,他抓出一个政治建军的先进典型,组织了个写作班子成年蹲在连队写材料。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变个角度就整出一个典型材料,经常上报纸、上广播,搞得名声很大。结果他这个人很快就被总部方面盯上了。大家看当时那架势都议论说,看吧,黄振中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干到总部去。但真到了总部来商量调人的时候,李冶夫却把黄振中攥在手心里,怎么商量也不肯放人。事后为了让黄振中继续安心在军区部队干,李冶夫还给黄振中提了一职。大家这下都看出来了,李冶夫是真的重用黄振中,舍不得放黄振中走呢。后来,李冶夫调到总部时,大家都以为他当时就能把黄振中带走,但却没见动静。大家又猜测等李冶夫在总部那边稳定下来后,立刻就会调黄振中去。果然,后来总部曾几次动议调黄振中,但不知为什么最后却都落空了。
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顺便去看望李冶夫,李冶夫刚好出去了,秘书让我在会客室等一等,我就与一个也在等李冶夫的人攀谈起来。他说你就是周汉呀,早就听说了一直没见过,李冶夫对你评价不错呀。我哈哈大笑,说李政委对我评价历来不怎么样,你是不是搞错了,说的是黄振中吧?他说没错没错,就是周汉嘛。黄振中我也知道,李冶夫对他的印象……怎么说呢?看我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他这才压低嗓音凑近我说,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李冶夫对黄振中是个什么态度,好几次提议要把黄振中调来,但都被他给压下去了。为什么?我吃惊地问。那人说,他也不说明理由,只扔下一句话:此人可用,但不可重用。你想……
我当时脑袋就像被灌进水了一样,啥也想不了了。
你再好好想想吧。黄振中说,我已经决定了。说罢,咳嗽着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我默默望着他的背影,心里不由翻腾起许多的感慨。黄振中的背向前佝偻着,使本来就矮小的身躯显得格外苍老、羸弱。我理解黄振中此时的心情。这场事故对他的确是一次致命的打击。那个典型是他亲手抓起来的,是他政治工作的主要建树,是他事业的一个标高。但那发炸膛的炮弹却顷刻间就毁掉了他多年的心血。最可怕的是,当硝烟散尽之后,他突然醒悟过来了,突然发现自己用多年努力构筑起来的并不是一座丰碑,而只是个毫无存在价值的虚华的牌匾!对我们这些视事业为生命的老家伙来说,这样的打击实在是过于沉重了。我始终认为黄振中并非死于肺癌。其实,当那发炮弹在炮膛中炸响之时,黄振中的生命就注定完结了。
李冶夫在得知这件事后,只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事故发生之后不久,一辈子没抽过烟的黄振中就被查出患了晚期肺癌。黄振中垂危的时候我去看他。当我告诉他李冶夫让我代为问候他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就亮了一下。当时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但他的嘴还是费劲地嚅动着。守在旁边的肖萍就俯在他身上,听一句转告我一句。他说,他这辈子最幸运的是两件事,第一是碰上了一个好领导,第二是找到了一个好老婆。肖萍在转述第二句话时忍不住哭了。
她不敢看我,我也不敢看她。我只觉得嗓子眼儿一下子就堵住了,像有什么东西似的直往上顶似的,顶得我喉头涩涩地难受。我怕控制不了自己,抬屁股就走了,连个招呼都没跟肖萍打。
那是我和黄振中最后一次见面。
那也是我和肖萍最后一次见面。
5
死了几个?我的声调都变了。
七个。电话那边报告说,死了七个,伤了五个,一共伤亡十二个人。连长当场死亡,指导员……
混蛋!我朝着话筒大喊了一声,就把电话摔了。
我和黄振中赶到现场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那门炸了膛的迫击炮阴森森地蹲在月亮地里,不怀好意地等待着我们。我简单地看了一遍,发现整个炮筒都炸飞了,这说明炮弹是在炮膛里爆炸的。但这枚炮弹为什么没有打出去呢,我冷峻地扫视着陪同在旁边的那些指挥员们,他们似乎个个都在回避着我的目光。
我明白,他们都和我一样知道这是操作失误造成的,都和我一样明白这是装炮弹时只顾了抢速度,把炮弹别在炮膛里炸了。但他们谁也不敢说。
我恶狠狠地瞥了黄振中一眼,真恨不得毙了他个狗日的。就是他非要搞什么迫击炮速射研究,结果弄出来这么大的事。死了七个人,七个呀,加上受伤的五个人就是整整一个班!当初提方案时我就不同意。我说胡闹,训练教程上怎么规定的就怎么练嘛,炮兵的任务是给我打准,不是给我打速度!但除了我,党委其他人都表了态,同意炮团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知道他们是碍着黄振中,因为这件事是黄振中一手抓的,别人一听说他准备让那个政治建军的典型连队来搞,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不管,我说那我保留意见!结果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