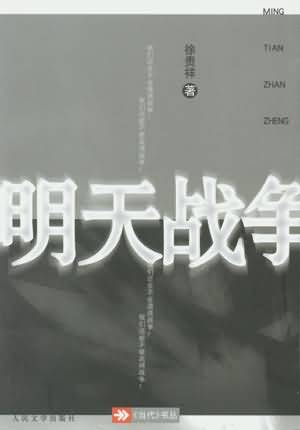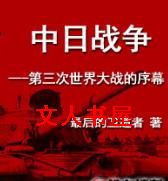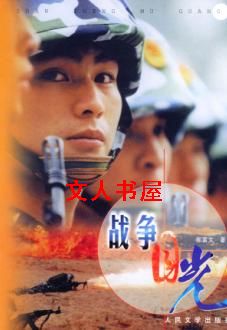采访海湾战争1416-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十二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我们几个轮着干。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五点开到上午九点半,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记者,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一百三,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鸣声。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江亚平大叫了一声“羊”,几团黑呼呼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本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汽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十万个太阳从三百六十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象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逐步前进。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上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可好歹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联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没面目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抢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55℃就再也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磐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怪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乐于助人,一辈子受用不完。其实当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象所有多梦的中学生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锲入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竟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六十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末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楼,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美国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辞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象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埃尔森彻(EL CENTRO)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白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就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如果没摄影部老板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冒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鲁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挂着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务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到处是朋友的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89年在北京跑过新闻,90年亚运会上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配写过文字。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事后,河野告诉我,新华社播发的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是各大通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华的照片,为此共同社摄影记者还挨了批。其实,假如没有河野校友告诉我德奎利亚尔行踪,我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机场,快速突破警戒线,更不用说拍照传真了。
1月14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唯一没办此手续的。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再次感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三十二、新闻检查
三十二、新闻检查
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克亲自主考。老鲍勃先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rut ”(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认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站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居然,不出两年,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送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躲着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我场场必到。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所有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的立场,因此没有什么麻烦。我成了地档道档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