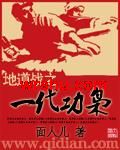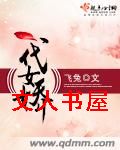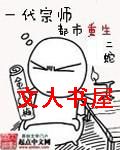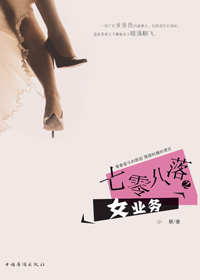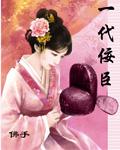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穿越天安门的时候,开始稀稀拉拉地下起了小雨,所有男选手默默地戴上了由支点公司赞助的安全套,有白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猪血红的、鸭屎绿的、黑乎乎的、五彩的、还有本年度主推的高科技变色安全套,点缀着整个裸奔队伍,充满了盎然的生机。
啊,这将是一次多么令人怀念的忧伤而色彩斑斓的裸奔啊!
我不看书
我有两个朋友,都是爱看书的人,一个曾经是我的室友,他的口头禅是,五四以后的书我是不大看的。掷地有声,令我很羞愧,因为五四之前的书我就很少看,当然五四以后的书也看得不多,只是按照我小人之心的逻辑,他的观点更多只是表示一种姿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起住,他也一样天天点灯熬夜看我的金庸全集。
另外一个是我的助手,他的观点是,只看旧书,从来不看外国书。每周必有一天去潘家园逛旧书市,风雨无阻。因为我年纪比他大,而且是他的领导,自我感觉有改造教育他的使命,当然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了批驳。他的论点是,至少经过十年时间的淘汰留下来的书才有价值,外国书被翻译以后就不是原来的书了,除非看原文的,但是他只懂中文。这很像我的口气,为了表示姿态,我经常对别人说,中国的歌我是不大听的,没有经过十年时间淘汰的音乐不是好音乐。
其实我已经好多年没正经看过书了,不是自我感觉牛比,而是感觉该看的东西太多不知如何下嘴。偶尔下了狠心准备看一本,结果发现根本看不下去,年纪大了,嘴太挑,脑子还受不了挑战,因此有很多书根本没法看。前一阵,在老婆的强烈推荐下看了一本韩国畅销书,我旗帜鲜明地决定一如既往地不看书了。
遥想当年我也是一个爱读书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理想是长大以后做一个出租连环画的摊主,我爸对我的评价是:如果他不在书摊上看小人书,就是在去书摊的路上。上中学的时候我看遍了学校图书馆所有的小说,(注,我们的图书馆非常小,十几平米的面积,小说其实也就百十本而已。)而且在课堂上、被窝里学习了大量乱七八糟的武侠小说。
俗话说,读书害人。对此我有切肤之痛。其中爱情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一直通过阅读的方式学习爱情,所以我的爱情观建立在书本语言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平庸琐碎,不值一提。而且在我的母语里没有适合表达“我爱你”的词汇,你只能说,我要跟你好,或者,我想跟你搞对象。粗俗而直白,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浪漫美丽感觉。我和我的早恋女友是通过写信的方式确立情侣关系的,当时我在书面语言方面的造诣已经完全达到了代人写情书的程度,甜言蜜语能肉麻死人。只是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突然感觉无比尴尬,根本不能进入爱情状态,用母语谈恋爱仿佛山西话的新闻联播,搞笑的成分远远大于内容本身。总之,母语毁了我的初恋。
后来我总结出来,当你越想表达深入的欲望,就要用越遥远和隐晦的语言,比如说“I love you”就比说“我爱你”要顺口;再进一步,做爱,这是一个外来语,make love,用标准中文说是性交、搞男女关系,和浪漫基本没关系,如果是各地方的说法就更加粗鄙不堪了;再进一步,SM,干脆只能用缩写了,在母语里要表述这个问题非常之复杂,“我想用皮鞭、手铐虐待你和让你虐待,通过这个方式来获得更另类更高的性爱享受。”话音未落,你已经被踢下床了。
我在大学里碰见过一些高人,我绝望地发现,他们几乎是在图书馆里长大的,要赶上他们,我得从头活一遍。最重要的是我的Fans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并不比我快乐多少,于是我决定自暴自弃下去。大学毕业以后我主要的文化生活是打游戏和听唱片,后来进了娱乐圈,大家都不看书,我也乐得随波逐流。
其实不看书也没有什么不好,又省时间又省钱,而且不需要用读书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尽可以不讲道理、耍混蛋。
为了表达我的决心,我制订了以下的不看书规则:看了两页还不明所以的不看,因为我最看重阅读快感;没看两页就知道他要说什么的不看,因为他藐视我的智力;和我意见相左的不看,隔着书不能和作者吵架会憋死人的;和我意见完全一样的不看,我还准备写一本呢;太有名的不看,全是炒作出来的;没名气的不看,很明显是垃圾嘛;文化人批判的不看,庸俗,没文化;文化人推荐的不看,假深沉、装大尾巴狼;太有主意的不看,话语霸权;太没主意的不看,自己还没想明白就敢出来混;点击率低的不看,群众都不爱看可见没啥意思;点击率高的不看,就不爱助长这种歪风邪气;斑竹推荐的不看,肯定是一伙的;斑竹讨厌的不看,因为被删掉了。
非自由撰稿人和独立音乐人
为了提高我的QQ点击率,我的自我介绍栏写着:自由撰稿人、音乐制作人。按照网络无真话的原则,你肯定猜出来我根本不是以上两种人,事实上,我是非自由撰稿人、独立音乐人。
如果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我会选择在秋天的下午写作,地点暂定在三里屯的街边,我支开笔记本电脑,就着一杯咖啡,一边看来往的美女,一边运指如飞地编着和她们的香艳故事。自由对我来说必须包括时间、空间和个人情趣。
这种待遇自我号称撰稿人开始就从没有享受过,编辑在约我稿子的时候一般都快火上房了:提高,明天务必早上九点之前给我,否则我就被开除了,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死存亡可都握在你手里了。你看,这种情况下,我好意思跟人家提自由吗。到目前为止,在行业里我的口碑都很好:从不拖欠,再着急的活都能按时完成。所以,但凡时间来得及,编辑都不约我的稿子。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甭管提前多久约的稿,都要等到截稿前一天的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动手写。
其次内容上是不可能自由的,稍微懒一点的编辑这样说,你写关于一篇三级片发展历史的,要搞笑的,不许提器官,不许细节描写,不许讽刺罗圈腿,因为我们主编是罗圈腿。稍微认真负责一点的主儿就费了劲了,把着电话能布置两个小时,恨不得连书写格式都告诉你:断句一定要正确,不该分段的时候千万别瞎分段,搞得跟古龙似的,这可是上中央台的,面向全国播出,出一点问题影响可就大了。末了,问:“你什么时候交稿?”我说:“半小时以后收信吧。”“这么快?”“你刚才说的我都整理完了,断句标点白送。”
自由这玩意儿没有的时候挺想要,冷不丁给你了还真有点不适应,上个月有个哥儿们约我写一篇,撒了欢的、可着劲儿的、低级趣味不限的文章。我立马起了戒心,是不是稿费比较低呀,按照我多年的经验,稿酬是和自由度成反比的,要么就是没谱的事,肯定80%会被主编毙掉。你知道什么叫“人之初,性本贱”了吧。
我有一份正经工作是做音乐,别人给面子都叫我制作人,在老百姓心目中,音乐制作人就是那个坐在一堆音响器材中间,留半长头发、风光八面、吆五喝六、再牛比的歌手在他面前都要称老师的那个人。可是我一直都没得机会正经当上制作人,老板不信任你,歌手嫌你没名气,实在憋得不行了,我立下志愿要自己做一张唱片,给所有人看看。于是终于沦落为独立音乐人。
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音乐制作现在是一个大投资、需要很多人一起完成的系统工程,各司其职,一个萝卜一个坑,理论上来说,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完成应该涉及到30人次,词、曲、编曲、制作人及助理、录音师及助理、乐手、歌手及助理、企划、文案、宣传等等。而在这张伟大的唱片《拉链门事件》里,我一个人包揽了以上90%的工作,为了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我们被迫选择在物质上的独立,没有投资,没有设备,没有工作人员,吃喝拉撒睡都要自己操持,本来三个月能完成的工作要拖两年。
我有一个朋友叫胡吗个,也算是著名的独立音乐人了,他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几乎成了北京最小的唱片零售商,恨不能天天骑着三轮给人送货。还有那些不著名的独立音乐人就更惨了,知道为什么北京的地下室入住率这么高,方便面为什么卖那么好吗,都是独立音乐人惹的祸啊。
有一个段子怎么说来着,天底下最倒霉的人就是炮兵连的炊事员,打炮轮不上,黑锅总是他背。想一想我的处境基本和他一样。但是在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保障之前,我不准备有什么改变,因为至少非自由撰稿人可以给你稳定的收入,独立音乐人可以让你享受有限的自由。
像肥皂泡一样飞
最近,我发现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低,只要下班以后能看两集美国肥皂剧,然后洗洗睡就挺满足的。我妈的要求更低,只要两集国产肥皂剧就打发了。我妈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肥皂剧素养的观众,配备很专业:零食一袋,手帕一条;情绪很到位:该笑的时候就笑,该哭的时候就动真格地哭。
我小时候还没有电视,我妈经常带我去看肥皂戏,在我印象中京剧像大片,总是表现大场面的历史风云,越剧和黄梅戏就是肥皂剧,老是家常里短的,小两口带一个丫鬟能哼哼唧唧唱一晚上,同样一出戏我妈能看20遍,每看一遍情绪都和第一次看一样饱满。后来经过台湾肥皂剧《星星知我心》系列的历练,我妈的肥皂剧素质基本炉火纯青,往往是哭一会儿,累了小睡一会儿,醒过来接着哭,一晚上用好几条毛巾,活脱脱一个情景悲剧。
早几年刚有DVD的时候,我陆陆续续买了好几百张片子,后来发现搞笑片、商业片全看完了,剩下的都是艺术片,有几部看了数次都没看完,每次看都跟新的一样,我的女朋友很敬佩地对我说:达令,这部片子你都看好几年了,实在看不懂就不要难为自己了。你看,为了追求进步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有了破罐子破摔的趋势,前一阵,一口气买了两套著名的美国肥皂剧《老友记》、《欲望城市》,每天看四集,生活从此充满了厚颜无耻的快乐。我想,我妈的遗传最终还是战胜了艺术。
最近我因为偶然的机会投入了一个国产肥皂剧的创作,通过对比,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为什么美国肥皂剧这么好看。首先它目的单纯,就是娱乐,这一点《老友记》发挥到了极至,让你可以从头笑到尾;其次是真实,没有那么多假模假式的粉饰,他们表达出来的情感很直接朴素,缺点和优点都很鲜明;再次是忌讳少,比如《欲望城市》专门探讨性的问题,《老友记》里也大量涉及这类在中国人看来敏感的问题。而在中国做事情就复杂多了,必须考虑传达什么、反映什么、扶持什么、打倒什么,还有很多“雷”根本不能碰的,比如性。
当然按照我妈的标准,现在的国产电视剧也挺好看的,人家有《老友记》咱们有《候车室的故事》,人家有《兄弟连》咱们有《激情燃烧的岁月》,人家有《欲望城市》咱们有午夜生理卫生专栏。
我计划让我父母退休以后来北京住。我爸严肃地跟我探讨,那我找谁打
麻将?我说,可以在电脑上给你安一个麻将游戏,天天都能玩。我爸说,那我赢了谁给钱。我又诱惑我妈,到北京天天都能看美国肥皂剧。我妈说,那里面有王秀花吗?
其实,我们的生活很难得会经历大片,大多都是鸡毛蒜皮的肥皂剧,而生命就像肥皂泡一样飞。
著名旅法音乐人
我的朋友金银财宝拍了一个艺术短片《一样的一样的2》,使用了我专辑里的一首歌《诗一样地射了》做片尾曲,为了自抬身价,他把我包装成了,说这张专辑是在法国做的。于是,招致了他的工作班底的无比敬仰,说,你看人家这音色用的,这编曲,这缩混,不得不承认,咱们国内音乐人还是有很大差距啊。
这让我心虚了好一阵,当时我顶多算著名旅西音乐人,因为我住在西四,和法国还是有一点差距的,没多久我搬到了马家堡,成了旅马音乐人,和胡吗个齐名,号称双旅马音乐人,不过他住在马甸。
去年我差点真的去了法国,而且是公费的,因为公司和法国有一个合作项目,邀请我们去考察,但是在办护照的时候我给挂了,按照常规,办加急的护照只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估算着日程差不多还有点富余,最终我失算了,因为我的户口在天津,那个地方特别官僚,说办护照的人太多了,取消加急。任我说破了嘴皮子也不理我,等我拿到护照,同事们已经从法国回来了。今年五一,我狠了狠心准备去个法属殖民地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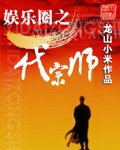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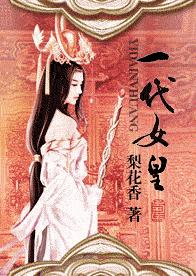
![[综]一代名师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9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