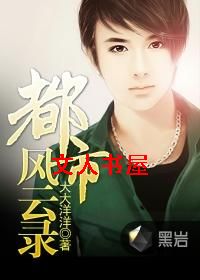һ����-��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Դ����Ҳ��ϲ������Ļ����ˣ���Զ���ּ������µĸо���С�����������Ų���Ҫ�������һ����ϲ�ϲ�������磬�ҸIJ����������ڿ������Ů�ӣ����Ƕ�ô���ģ���ô�Ե����֣�ÿ��İ���IJ��˶������������Ѻ�һ���������¸ҵ�Ц�ţ����������ս���⾫����ʲô�ط����ģ��ڶ��������ˡ�ʹ���ѹ����ǣ��������й����������˰���������������ҽ�����ҳԣ���ĬĬ�Ľӹ��ˣ�ҧ��һ�ڡ���θ�ڲ����ã�Ҳû������ӣ�������ô�ã��������ܲ�����ѧ�����Գ��еģ������ﲻ��ֻ�й��Ρ���Ȼ�ҵı���һ�ᣬ�����������ˣ�����û�о��棬ֻ��һ������ı��飬�·���֪������ӵĺ���������Һ���������֪���������Ҫ���Ҵ�һ�㣬������Ҳû���ʸ���ô����
���ӳ����ˣ��Ҳ��������ᡣ
��˵�������㰮��ʲôС˵�������Ҵ�����㡣��
�ҵ�����˵�����Ҿ�Ҫ��Ժ�ˣ����ÿ�����
��Ǹ���˵�����Բ�����ô�Ҵ��㻭�����ɡ���
�ҵ��ͷ��
����Ȼ�����˸�ʽ�����Ļ���������ͷĵݸ��ң�������ָ�ǰ��ģ��˳��ġ��ҵ���˵
�������̫���ˣ�лл����
��Ц�ˣ�����˵����
���ʣ�������գ���
�������ơ�����˵����������һ�����֣��������Ѷ������ơ���
����С�㡣���ҳƺ��������������Σ��μ���������
�����ͷ������úõ���Ϣ�ɣ�����̫�࣬����ԺҪ�������壬Ǯ��������εģ���Ҫ�����ǽ�������
���ĺû�����һ�кû�һ������û������ҵ��ġ�
�ٹ�һ�죬�Ҿͳ�Ժ�ˣ��Ҵ������Լ����·���վ���ſڣ����ýŲ��鸡���ʴ˵ȼƳ̳�������ȥ�˹�����������С�����ˣ�������һ�����ܷ�����������Ц������æͣ�˳����߳�����
�����������Ժ�ˣ�������˵�����������ȥ��������
����Ϊ�����ĵ�Ե�ʣ�������ϡ�
��Ц������������ˣ�������һ�̡���ʲô��ϵ����
�Ҳž�����������ȥ��С���������������ij��ӡ�
����������ʡ�
����������ɣ�����Ҳ�ʡ�
��û�е��¡�����Ц���������ҵĹ�������
��ֻ��˵��������ٽ֡���
�������������ᣬ��������ѧԺ�ģ���������һ�ۣ���������ᣬ����˶ʿ�ˣ���
��ֻ��Ц�������Ǻ����������ֻ�б�ҵ���ſ���ס��
���Ӻܿ�ĵ���Ŀ�ĵأ���������л����һֱ������ܿ����������������˵ģ��������������ȳ�ϣ����
�һ������ᡣ����һ�������գ����硣�����Ȼ�ܺã����ʵ������ҵ������ϣ���һ���ɫ�Ļң�һ���ο���̯���š��һ��������ڴ��ϣ�ҽԺ��һ�ж�������ġ�����ҩˮ��ζ�������Ŵ��������еĸо������Ǽ�į����ģ��ҵ����컨�壬ÿ���������ij�ȥ�ˣ�����������ȥ�أ��Լ�һ���˳�ȥ������Ӱ�����ư�ȥ��һ���ƣ�������������Ů�ˣ���һ����������ô����û����˼��
��ĬĬ������ë��ȥԡ����ԡ���ط��任��˯�£�ǿ���Լ�˯�ˡ�
Ҳ��ͬѧ�����ţ��ʺ�һ���������ˣ�Ӣ�����Ƿdz���ɨ�Լ���ǰѩ�ġ���˯�ڴ��ϣ�����˼�룬����������ֹ�ڴˣ����ֲ����漪�����ֲ�����ë�£�������û���Ž���Ƶķ�ʽ����ֻ�÷��
����Խ��Խ��į�ˣ���ǰ���ڴ��ͥ���ô���֣��������Űܼң�������������Цŭ���Ǯ��ѻƬ��Ϸ��ȢС���ţ�����һ��������������
������Ǯ�˵����ӣ�Ǯ�����ˣ�һ��Ҳ���ˣ����ö��Խ���˸����ö��Խû��Ǯ��ʲô��
���ھͲ�һ����������̫�����Ͻ������ǿ���Ц���ڼң���Ľ�ҵ��˻��治���ء�ȥ�������һ����������д�ţ��������������״�������һ�仰��������ҵ�ָ���ں�˭���ҵ�ָ���ں��㡣�����ҿ��˵�û�����絶�ֻ�Ƿ���һ���Ӵ���
ѽ����Ը���չ�����������û���������������ܹ��ı����ǵĹ۸��أ�
��ѧ�ñ�һ������ᣬû�г�����ζ�����Dz���֪����Ļ�ģ����������������һ��Ĭ�������ղ�����Ҳ����������������˼����ϵ����������ǿɲ���Ц����������û����ຣ������ֻ�пɲ��ĸо���
�ҷ·���˯���ˡ������ּ�������ǰ��Ů���ѡ�������ֻ��ʮ���꣬ѩ�����۾�������һ������ݡ���Լ�����ڴ���õȣ�����һ����ʱ��Ů���ӣ����������缸���ӣ�����һ����ɫ�۲��Ķ�ȹ�ӣ��߸�Ь��ת��ͷ��һ��Ц����ӭ��ȥ�к�����
������ͷ�ı̺����죬�����һ�㣬��ӭ��ȥ���������֣�Ȼ���ұ����ˡ�
�����ڴ��ϣ���ɫ�Ѿ����ˡ�Ӧ������������ң������ˣ�Ҳ�õ�����ȥ�Է���
���ڻ��·���ʱ�����ؼҺ�Լ���������衣��һֱϲ�����衣�ҿ��Ժ���ò����������������˵��ԭί�����Բ������ж��ٸ����ӡ�
���õķ���Ȼһ��ζ������ĬĬ�ij��š����ڰ���������ң����������Ҷ��档Ӣ��Ů��ʲô���ã��������Ӽ����á�������˹�ٶ��и�Ӧ��Ů��ζ����
�Ҳ�ϲ�����Ů�ˡ�
��˵�����㵽����ȥ�ˣ��ü��첻���㣬�������ˣ���Ů���Ѷ��ڷ��������ѧУ��û��ȥ��Ϊʲô��һ���������ù��ġ���Ϊʲô���Ʋ��֣������㣬���ģ�ʲô���£��Ҹ�Ů���Ӻȱ����������û���ˡ�������ò��ã��˵�á�����
��û�лش𣬳����˷�����˵�����Ҳ��˼��졭����Ȼ����߿��ˡ�
��֪������ô�롣�Ҳ��ܹ�����ô�롣���죬�����˲����������ǿ��ģ��Ҽ�į�����Լ�֪���Ϳ����ˣ��ҷ�������Ҳ�Լ�֪���Ϳ����ˣ��Ҳ���չ�����Լ����ҵ��ģ��ҵķΣ����ڴ�����ʲô�����ڲ�����ʲô�����������ء�
�ҿ������ߵ硣��ֻ��һֻСС�����ߵ磬���������ģ���úܡ�������ţ�̨�����졣��ǰ��һֻ¼���������Գ�ʱ����¼���������������ˣ���Ϊ�κ���ˮ��������ǣ�������ס����ߣ���ë��͵���ˡ�����Ů���Ѷ���ǰ�͵ģ�������ò����ˣ��������������˻��Dz��ϻؼҡ������¶��ء�
�������������˹ϣ���������������ӹ��������������������Ȼ�Լ���˵���������������СС���й�ͷ����ʲô��˼���������˼��й����й��̵ģ�����֮���ˡ����ǻ���������
�����Dz����ġ�
��ʱ����ڰ����������Сʱ��̨���յ���ɫ���죬������ô���ۣ����ǹ��β���ֹͣ���Ƶ����졣
�����ֺγ�û������Ĺ��Σ��������Ƶ�����ϣ������˼ҷ���������ҹҹ���ߣ����й����Ѻ��ж����������磬�һ��Ƕʼɵ���ʹ���ҵ�������ʹ����ʼɵ���ϣ�������
�����ָ������ˡ�
ȥ��ѧ��
������Ϥ��ţ�п㡢���¡�ñ�ӡ�����ȥ��ѧ��������Щ������ͬѧ����ף����Ǻ��������Һ����ǡ��·����������µĶ�����ͬѧ����������������һ�մ�һ�Ż��������
�Ҳ���ȴ����졣
��һ��Ů����д�˶�ר����������������������Զ�ǵõġ������ճ���û�д���ϣ�������䲢û�д���ʧ����������д�����Ǻá�
�пյ�ʱ���ұ�д�ռǡ�
д�ռ���д�Ŷ��������į�ľ�ֹ��
������Ҳ�ǡ�
�����ε�ʱ����̾һ������ʹ���������վ���ſڣ���Ҳû�й����к����������Ҷ�ôԸ��������������һ���ÿ���Ů���ӡ�
ͬѧ��˵�������������ڲ��ˣ�����̫���ˡ���
˵�ĺ��ǣ�����̫���ˣ�û�У�û��̫�࣬����̫���ˣ���ѧ��ѧ����һ����������·�����˿��ң��ó��ʼǣ�һ������ʼ�����������Զ��ģ��������������ƶ����������Σ��ڿ����ϰ����еľ��Ӵ�����ġ�
�������ֹ���һ�����ڡ�
һ�շ�ѧ���������ᣬ�����������ң�����¥һ������һ��Ů�ӣ���ʮ�־��죬����ϸ�ˣ�ȴ�в������������Ҳ�û�������������������Dz�����˼�г�����
��Ц��ӭ�������������ƣ��ǵ��𣿡�
����С�㣬���Ҳ�����˼��������ô���ˣ���
��������ѽ����Ȭ�����𣿡�������˵��
��ǩ������������¥ȥ��������ˮ�������ҡ�
�����ȳ��dz������ĵģ���˷dz��������˳�������ȹ�ӣ�ͷ�����Ƕ̶̣��۾��������⣬��ʹ������̤ʵ�ĸо���������һ�𣬺�ƽ����
�����˶�ʮ���ӣ���˵��������ÿ����һ���ۻᡢ���������ˣ������Ǻ���ѧ�������ҼҾ��У�������пգ�������������
�����룬�����ȥ�ˣ��������ǵ�һ���ӣ��Ͳ�ϡ���ˣ�����ÿ���˶���ô�á�
��������ḣ��������Ա�𣿡����ʡ�
��������������ҵ����������С������˵˵ЦЦ��������һ�졣����ÿ������һ���棺�����γ��迴��Ӱ�������ɵģ����ϲ��Ⱥ������ٺ�Ҳû���ˣ�����Ƚϰ�����Ҳ���Զ���һ�ǿ��飬û���˻�ɧ���㡣��
��Ц������ô����ɳ��Ů�����ˡ���
��ҡͷ������ô�ң�ѧ������������ܾ�������ǰҲ�й����־��飬����ܹ���һ�𣬵�Ȼ�Ƚ�����Ӧ����
��ΨΨŵŵ��Ȼ��������ˡ�
�Ҿ�������һ������ֵ�Ů�ˡ���Ͳ�С�ˣ����úܺÿ����ֲ����˼ҵ�̫̫����ͷ�������ĵغ��ƣ��������ģ�û�й��������Ǹ�ʲô�ģ��������⡣
���������Ŀ�Ƭ���˿�����ַ��һ���߹��סլ����
Ҳ���пյ�ʱ����ȥ�������������Ҳ�Ҫ��ĩȥ���һ�����������������ȥ̽������
������2��
��Щ����������������Ů�ӣ�����ѧ��������ѧ����Ҳ�м����˵�̫̫����һ�ݼ����鹤����Ҳ�����˲����Ů�̡����������������������С������û�����dz�������ҽԺȥ���˼��죮����һ����Ҳ�������ġ�
�ɺ��ǣ�����û��������ʲô����˿��֮�࣬ʹ������õĽ�ڡ�
��Ȼ����ʲôҲû�У���һ�����������һ���ȥ�ˡ������ܲ��ڼҡ���������һ�����������Է�����������ģ�˵���������������ã���ò��ͷ�����Ѿ��������ֲ��ض���������Ρ�
������û�г�ȥ��
��������ǰ��õ�塣������һ��С�����ϣ����ϴ��źܺ�����ס���ʱ�������ո��е�ů�ͣ���ֻ��һ��ë�±��ģ������dz��㡢����������������ͨ���·����������ϣ��������˿���ȥ�������
�ҳ�����һ�����������ȥ�к�����ȴ��������û�ж��ּ�������ֻ���������ﲻ�����·��Ѿ����˺ܾ��ˡ��ҺܳԾ���ע�������ı�Ӱ��ƽʱ�������볯�������ˣ���������Ӱ���Ǽ�į�ġ�
��ô�ˣ��Һ��Dz��죬�����־����Լ�Ҫ����ߡ���һ�����ڼң��ѵ���������Ц���ɣ�
���������һ��������С�㡣��
��̧����ͷ��ת�����������������ң�����վ����������ѽ������������ô���ˣ�Ҳ��Ԥ��֪ͨ��һ������
���ҡ�����˳·�ġ�����˵��
���Ҳ�����һ���ӹ������ۻ��ˣ��������أ�û�����������Բ��𡣡���˵�������������������̬����Զ�ܺͰ���ȴ������ʧ�������֡�
�����������ӡ�����װ�ε�Ư�����ˣ���������һ������һ�ִ����������������˿��ȣ��ó��˵��ģ�һ�����ҹ���æ��æ��
���·�������ﵱ�����ļ��ˣ�������������������Щ���ǡ�����ò�����ţ�һ����ʹ���ı��飬С�����������ű��ӣ���Ҫʹ�车��������Ȼ�Ҳ�֪�����Ѿ��������ˡ�
����һ���ˣ������Dz�֪�����ġ�
һ�ֲ����ܣ������İ����Dz��Ծ��ģ��ȵ������Ժ��Ѿ�̫��̫���ˡ�Ҳ���˰��ò�һ������ֻ������һ��ǿ����ռ�е����������ÿ죬ȥ��Ҳ�죬һ������Ӱ���١�
��ǰ��һ��Ů���ӣ������������ֵܣ������ֵ��������ߵ���һ�գ���˵����������ţ�����С˵�����ݵ�һ�����ҵ��ģ�����һƬƬ����˵����ʱ�����������¡�����������£���������֪�����Լ��ڿޡ������ദ�ò����ã����������ֵܻ���ʹ�Է������ǵȷ�����ʱ����̫���ˡ�
ÿ�ξ������ֵ�ס�����ᣬ�����絶������˷���������֪����ʱ���Ѿ�̫���ˡ�ÿ��д�ţ�ֻ�����ᣬ����д�����ţ��ֲ��ij����ҵ�ʱ����֪�����Ѿ��������ˡ�
��ϸϸ�Ŀ����������ף������֣���������
��˵��������ô���������ţ���������һ�衣��
���ó�һֻСС��¼���������ˣ����ڶ��ߣ���Ȼ֮�䣬�������Ǻ������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