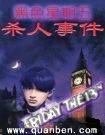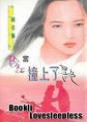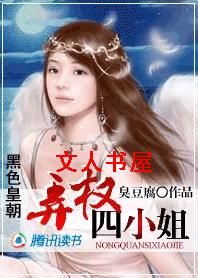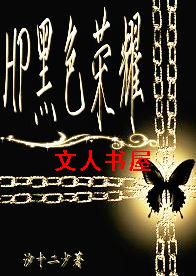黑色念珠-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罗先生?您说是罗水泊……他怎么住院啦?”
“患了癌症,前两个月才查出来,许多医院不愿意收这样的危重病人,还是几个朋友拐着弯儿,托了关系,才让他住进了协和医院里。”
我愣住了。
“什么—;—;癌症?”
“是呀,而且……癌肿已经堵住气管,说话不清楚啦。”
“我要去看看他!”
“算了吧……让人很难受的!”
“不,我一定要去!”我拽住了徐明远的胳膊,冲动地说:“您告诉我……他的病房号码,让我再见他一面,好吗?”
徐明远看我一眼,默默取出一个笔记本,撕下一张,飞快写下了罗水泊病房的号码。递给我时,嗓音沙哑:“你要去看他……就得赶紧!我听医生讲,他恐怕是过不了这个星期啦。”
我什么也没说,怔怔地望着他。他又在滚滚的人流与车流中消失了,淡白色的背影像是一团雾气。
在刹那间,我的脑血管似乎被一把奇怪的剪刀割断了。使我再难以回忆起某些事件,也想不起哪些生动的细节,我的思想只被割裂成为一块又一块的空白。偶尔,那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又浮现了出来。真的,当时我既没有感到悲哀,也没有感到怜悯,自然更不会意识到他有多么伟大。我只是下意识地想到了,那一条冰冷冷的线终于穿透了他的苦难命运,到达了顶端。那就是死亡,它才不去考虑什么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性呢。
在此一年前,我到老牌坊胡同的那间极狭窄的小屋里去看他,我没有敲门,因为看见房门微掩着,就忽然推门闯进去了。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将木板床的铺盖卷起来,正趴在上面写着什么,旁边堆满了各种书籍。他摘下了那顶著名的旧呢帽,满脑袋是蓬乱的花白头发,见我一下去闯进来。他很紧张受怕,神经质地收起稿子,又顺手将两本书压在上面。
一会儿,看清楚了是我,变得异常兴奋,甚至和我拥抱了一下。站在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我找不到地儿坐,只能站在床边跟他聊天。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破皮箱,还有几个硬纸箱子。电灯泡拉得很低,几乎垂到床上。罗水泊解释道,这是徐明远帮他改造的,在电灯泡上加了一截电线。由于他天天晚上要读书写作,眼睛却不好使了,只得将灯泡拉得近一些。
他很快收拾起了床板上的手稿与书籍,瞥了我一眼,说道:“陪我到街上散一会儿步,好吗?”
我们俩,一老一少,就一边走一边随意聊着,从那条小胡同一直走到了朝内大街上,足足散步了两个多钟头。罗水泊走累了,就一屁股坐在马路边,仍然不减谈兴,两只手激烈做着手势,很大嗓音地问我:“你说呢……你说呢?”
他看到一群中学生在路灯下聚在一块儿抽烟,又突然问起我们在干校打群架的情形。他津津有味地问了许多情节,还有我们那时的心理状态,他背起手,插了一句嘴:“也许,这也是一种生命力的扩张吧……”
“你们为什么要视此为光荣呢?”他怀着极大好奇心问我,又自言自语:“唔,唔,这可能是因为时代的烙印!崇尚暴力、战争等等……战争就是许许多多人在打架嘛!”
他又问我,现在还学英语吗?我很悲观地说,我不想学了,即使学会了英文又有什么用?难道还能让我们去美国吗?
“不对!不对!你说得太不对了!”他显得很激动,摇动着我的肩膀,“你千万别相信那一套!读书终究是有用的。社会需要人们去建设,更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你应该学外语,你应该学历史,你应该学许许多多知识……”
“可是,”我带点抬杠的意味说:“我只有一个脑袋呀……”
“哈哈,脑袋!”他笑了,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用手指一指旁边的房屋,“你看看这间房子,很高大,很宽阔,是不是?”
“是呀。”我不明白他调转话题的用意。
“能盛得下多少东西呢?几十立方米,几百立方米……也就到头了!你说对不对?”
“对呀。”
“可人的脑袋呢!它的体积能塞进多少知识……告诉你吧,我现在每天的阅读量起码是十万字以上,一百天是千万字,一年要将近四千万字!那么,你来猜一猜,它的最终容量是多少呢!”
他忽然将脸转向我,用手指点着脑袋说:“它的容量是无限的!”
第二天晚上,我到协和医院—;—;当时叫“反帝医院”去看望罗水泊。他住的那个病房很难找,并不是在病房区里,却是在某个试验室旁的一个小房间里。走廊里灯光暗淡,我转悠摸索了好久,才找到那儿。后来,听徐明远说,由于罗水泊是未摘帽子的“右派”,一直不敢收他住院,将其撂在急诊室的走廊。罗水泊的一位老朋友听说了很着急,不顾自己双目失明,拄着拐棍去找了在医院当领导的亲戚,走了一些门路,才把罗水泊收留下来。
这个小小房间不到十平方米,只放得下一张病床,一个白漆小柜子和一把椅子,旁边同是挂点滴的木支架、高压氧气瓶和心脏示波仪等医疗器械,许多的管子联结着他,他就像一个蜘蛛网里的受捕物。我进屋时,徐明远正打算摆放他的行军床,房间是那么狭窄,只好将小柜子搬到门外,才能把行军床放下。
他带我到罗水泊的病床前,罗水泊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好似一个骷髅。他的黑瘦脸庞没有什么表情,只是连接着鼻饲管的鼻翼轻微抽动一下,徐明远凑近他的耳旁说了两句什么,罗水泊的眼睛慢慢张开,忽然,他的瞳仁里闪出了亮光。
我凑过去,强压住心头涌上的酸楚,喃喃地说:“罗伯伯,罗伯伯,我来看您啦……看您!!”我又拉住了他的一只干枯的手。
他枯瘦的脸上漾出了微笑,嘴唇嚅动了起来,像是想跟我说什么,喉咙间咕噜噜响。他又示意徐明远,要他为我解释。徐明远费了好大功夫,才弄明白了他的意思,皱起眉头对我说:
“他可能是说……要让你摸他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呀?也许是我没搞懂……”
我却一下子懂了,再也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骤然涌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徐明远有些奇怪地问我。
“噢,没什么……”我擦着眼泪,捧起罗水泊的枯瘦手掌亲吻了一下,又轻轻地在他的前额亲吻了一下。
罗水泊的眼睛望着我,湿润了。他的瘦嶙嶙的身体颤抖起来。这时,徐明远在后面轻轻拽我一把,暗示我该控制住情绪,又轻声说一句:
“行啦,行啦……时间太长了,医生和护士会有意见的。”
我又望一眼罗水泊,他仍然定睛望着我,有一滴极细小的泪珠从眼角淌落。我却哽咽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向罗水泊挥一下手。
徐明远陪我在走廊里走了一程,我们默默无言。
到拐弯处,徐明远声音很低哑地说:“直到现在……他的两个儿子和女儿,还不愿意和他见面……”
我的心似乎被揪一下,看他一眼。
“……医生说,他挨不过三天了……”
果然,第三天晚上,罗水泊就死了。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三章
如今,电视里出现了一些荒诞派手法的电视剧,让那些穿着古代衣冠的人们走进现代生活里,这真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虽然,也有许多观众表示反对,可我觉得,这要比“戏说”这个,“戏说”那个,要严肃得多了。由此,我产生一个奇异的联想,要让罗水泊生在明朝,或是生在汉朝,那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他大概很像司马迁吧。
当然,他没有受过宫刑。他发愤著书,产生一些新思想,却是绝对很相象的。尤其,他的一些书信,日记摘抄,其中的许多格言警句,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也是极相似的。假如作为一个古典儒生的罗水泊,头上挽着发髻,宽袍缓带,反而更能表现罗水泊的性格本质。而现实生活中的罗水泊,穿一件黑色破棉袄,腰间扎一根草绳,满脸的胡子茬,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还在脑袋上扣一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却是一种不中不洋,不农民不知识分子,不古典不现代的怪样子。他的思想也是这样,我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一面研究西洋历史,一面又研究中国的明、清史呢?他为什么对晚明史那么感兴趣?
我问宋英夫先生,他也沉吟不语。
有一天,宋英夫先生却突然问我,我问你,历史究竟是什么?
哦,我没想过……它到底是什么呢?
它仅仅是过去了的一段时间吗?或是已经消逝掉的一段空间吗?
当然,不光是。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我们现在总结出来的那些结论吗?谁好,谁坏,哪些事情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或者,干脆就是这个重大事件,那个重大事件……
那只是评价,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宋英夫频频点头,对的,这其实也是罗水泊提出的真正问题!我们不应该说,历史是怎样,怎样的,那就是真正的历史了。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天与地,人与兽,动物与植物,生存与死亡的不断生长过程。它的最后归结是沙子,是空气,是宇宙……
我看着宋英夫,发现他从来没有那么激动过。
他不再说什么了,紧抿着嘴唇,眯缝着那双细细的眼睛,怔怔地盯著书桌上的那个明代所制的景德镇瓷瓶,这是文革抄家后发还给他的少数珍藏文物之一。
宋英夫突然想起,十几年前,他们在五七干校一年后,他与罗水泊被抽调去放鸭子的那一段时光。他们那时常常谈起历史来。可是,十几年后,这段日子也成了历史啦。
早晨,天蒙蒙亮,他俩就带着一口袋馒头、六个咸鸭蛋出发了,手里拿一根长长的竹竿,脚蹬长筒雨靴,身后跟一大群嘎嘎乱叫的雪白鸭子。英夫的怀里揣一本《宋词选》,或是《宋诗选注》什么的。罗水泊呢,永远拿一本封面已破烂的《明季南略》或是《明季北略》。他们把鸭子赶到湖里,然后分工。在湖里由罗水泊放,在岸上由宋英夫放。
罗水泊挥舞看长竹竿,将那顶破鸭舌帽拉得低低,几乎压住了眉毛,他冲英夫点点头,说:“你先看书吧,这儿,我来。”他划着舢板,又赶了那一群鸭子先走了。
英夫选一块地势高的土坡,铺上芦苇,躺那儿静静翻看《宋词选》。周围一大片黑森森的芦苇,细风梳理着苇叶沙沙响,到处是残落的荷叶和枯萎的莲蓬,风儿送来带水腥味儿的苇叶香,又混杂了带腐殖质臭味儿的泥土气息。他最喜欢苏轼的那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寺寓居作》,在醉人的泥土芬香里,他喃喃念着:“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一道极刺眼的阳光斜射过来,他闭住眼睛,嘴唇轻轻嚅动,似乎在咀嚼那一道暖烘烘的阳光,又酸又甜的阳光。
罗水泊在那边又吼起来了,哇啦啦在唱京戏《文昭关》的那一段:“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英夫微微一笑,不由得放下书本,两臂抱着后脑勺,痴望着湛蓝的天空、远远灰白色大片湖泊,东摇西摆的芦苇丛……他这时什么也不想,人仿佛和天地融结在一起,也成为一丝风,也成为一缕云,也成为一块泥土。他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正我逍遥处。”
这时,一个人内心的宁静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人问他:“你的一生中最宁静、最淡泊的是哪些日子呢?”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哦,是在五七干校的那些日子里。”也许,会有许多人感到吃惊,却是真的,被发配到湖北农村五七干校的英夫,就好像是陶渊明,真正归隐田园,来到了桃花源里了。他似乎真正找到了那种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乐天知命,安贫乐道,淡泊无欲。那一场又一场时代的狂风骤雨电闪雷鸣夹杂而过,将他惊骇得简直是七魂六魄俱散。他的温暖家庭也摧垮了,老婆一封信接一封信寄来要求离婚。他那时就想过,唉,一辈子就待在这里,念念唐诗宋词,吃饱了肚子,还能欣赏湖光山色,也是满幸福嘛!
罗水泊的脾气却总是怪怪的。他不会享受这乐趣,从软塌塌的污脏帽檐下望去,他的脸色老是阴郁的,难得见他笑一笑。轮到罗水泊休息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皱巴巴的工农牌香烟,一支接一支凶猛地吸着,拿出那本《明季北略》,盘腿坐那儿,仔细地读着。翻一页,他狠狠吸一口烟,又往上神一神帽舌,免得帽舌又搭拉下来,遮住了眼镜。英夫见他这样子,好笑地问:“你干嘛总戴这顶帽子,把它摘掉行不行?”罗水泊蓦地一惊,呆呆望他一会儿:“哦,习惯了。就这样,习惯了。”
水泊把手指间夹的香烟狠吸了几口,又把那本发面饼似的《明季北略》推开,他嗓音沙哑地说:“英夫呀,看到崇祯皇帝临死的这几段,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