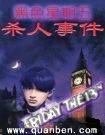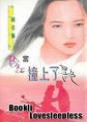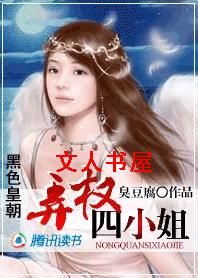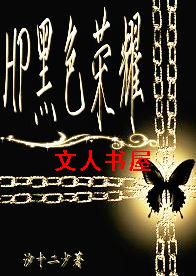黑色念珠-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故宫博物馆出来,这位英国老头儿另有约会,坐一辆出租车走了。英夫要去景山公园,我也跟他一起去了。在散发淡淡脂香的参天古柏间,我俩转悠一会,又顺着蜿蜒台阶,爬上万春亭。极目望去,紫禁城、前门楼、后海以及幢幢高楼都在雾沼中仿佛变为颗颗的盐粒晶体,在朦胧之中若隐若现。
英夫捧着下巴颏,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唉,在五十年代,我和水泊经常到这儿来。水泊写了一部《崇祯皇帝传》,没有写完。在那种文化气氛下,他是没有办法写完的。他笔下的崇祯皇帝,不仅仅是一个末代皇帝,关键的,是一个有痛苦复杂心灵的人。这个皇帝,自认为要对整个封建王朝负责任,肩上担了太沉重的担子,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最后,还是失败了。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很同情他。在观妙亭,一九二○年曾经为他立过一块碑,上书:“明思宗殉国处”。
我点一点头说,那块碑似乎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掉了。
是呀,以前水泊和我在那块碑前谈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崇祯皇帝严重的性格缺陷是刚愎自用和猜疑,致使对政事措置失当,朝令夕改,赏罚不明,又加派沉重的赋税,置老百姓死活而不顾,最后导致了政局的不可收拾。作为当国者,他不能不负责任。但是,更多的责任实际应该归他的父亲和哥哥来担当。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很有道理的。崇祯登基后,人心已坏,国势已衰,各级官吏的全面腐败已造成了明王朝的崩溃形势,他却仍然不气馁,企图拯救危局,殚心治理,若昔撑持十七年,颇不容易啊!这在亡国君主中实在少见啊!
这么说,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双重性格”,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啊!
确实如此。说这个人很奇特,就在于他从来不是个庸懦无能的人。他的性格很刚强,从不沉溺于酒色,孜孜求治,费尽心机只想搞好国家。史书记载,田妃的父亲田弘遇为讨他的欢心,把大名鼎鼎的陈圆圆献给他,面对这个能歌善舞的绝色女子,崇祯却心不在焉,没有一点儿兴趣。因为,他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太沉重了,充满无力回天的苦闷。他又不想干脆放弃这种责任,今朝有酒今朝醉,国事管他娘!甚至想跟命运拗一下,再做一个中兴之主。实际上呢,他又发觉自己的能力是多么微弱。我想,这种沉重的心理压力不能不使他的性格更加复杂,他猜疑多变,暴躁残虐,也反映了情绪的抑郁和阴暗。
哈,这也是一个君主的“痛苦人格”呀,也是儒家伦理道德这片土壤中滋长出来的!
那种痛苦心情的极点,就是他自尽于景山的前夕。这位性格刚毅的末代皇帝,几乎神经错乱了,他挥剑杀死了袁妃,又杀了他的幼儿昭仁公主和几个嫔妃。他要去杀皇后,皇后掩面疾走,回宫殿后自己上吊死了。女儿长平公主吓得痛哭起来,他哀叹道:“不幸生在帝王家!”也一剑砍去,女儿举臂遮挡,右臂砍断昏倒在地。他杀她们,自以为是爱她们的表示。他不愿意让她们落入农民军手里,再受污辱。
真惨!
当时,农民军已攻入内城,崇祯皇帝亲自跑到前殿鸣钟召集百官,无一人响应。他手下的那些大官们和亲信太监都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准备,当然不会理他。他也只好跟太监王承恩跑到了观妙亭那儿,赤足轻衣,乱发盖脸,与王承恩相对,在一棵老槐树上吊自杀了。临死时,他在衣襟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自己得罪上天,便遭天罚,都是诸位臣子误了自己。自己没脸去见祖宗,应自去冠冕,用长发盖脸。尸体任人分裂,但不要伤百姓一人。他的心情是极为凄凉的!真有点儿死不瞑目。
一幕悲剧结束了。我摇头叹息说,崇祯皇帝的一生应该说是一场深刻的悲剧啊。
问题不在于此,崇祯皇帝个人的悲剧结束了,而中华民族的悲剧才刚刚开始!崇祯皇帝的死亡,明王朝的崩溃,并不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换来一个新时代啊,接踵而来是一场民族的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勾引满清异族入关,然后,就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大屠杀和大破坏呀。农民军和满清军队与南明军队,以及各式的杂牌军队厮杀一团,凶猛的满族人为镇压反抗,常常采取屠城政策,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江阴屠城,一座又一座繁华的城市顿时被夷为平地!清史记载:“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有时,走数百里路,不见一户人家!又加上满族统治者摆脱不了落后的游牧民族习俗,大量圈占土地,更破坏了社会经济,使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下倒退了几百年!
宋英夫沉默了,用瘦骨嶙峋的手缓慢抚摸着皱巴巴的面孔,迷惘的目光又转向亭子外面。太阳已经从厚厚的灰云层中挣脱出来了。由灰而白,准备喷射出凝聚着的光芒。近前的一片松柏树,变得青翠欲滴。而远处雾色朦胧的城市,更像深浅不一的荒岗,影影绰绰露出来。可以看见红墙黄瓦的故宫建筑群了,那些宫墙、护城河、角楼等建筑还很模糊,却能隐约见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黄琉璃筒瓦了,真是金碧辉煌,豪华壮丽。在雾的轻纱下,车流汹涌的长安街更仿佛是一条灰色长蛇在蜷缩爬行。
我望着这座突破了迷雾的古老城市,内心出现了一种宁静又略有点儿虚幻的心境。又一种幻觉,我似乎立即就能目睹极为气势磅礴的景像,是从九天倾泄下来的汹涌瀑布,还是一个绚丽斑斓的美丽世界,还是别的?
宋英夫又转过脸孔,用手轻轻拍打着膝盖,对我说,历史的发展是莫测的,它常常会出现一些转折—;—;既是偶然又必然的,就深刻影响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对,我记得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有一个看法,若是没有满清异族的入侵,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中国有可能较早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这就是所谓的“萌芽”说,这个观点在史学界影响很大。大多数人赞同这个说法,或许是因为毛泽东的论断影响而成的。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些历史学家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搜集了不少资料,例如工商业已经迅速繁荣起来,许多具有纯粹商业性质的市镇在发展,市民阶层对封建官吏超经济掠夺的反抗,明清统治者实行某些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改革等。他们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样的萌芽再发展下去,就是资本主义了。
哦—;—;为什么这些萌芽又没有发展起来呢?
就是这个问题啦!水泊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的看法。假如说中国封建社会可以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就是忘记了资本主义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属上层建筑。而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有时上层建筑更能起反作用,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或生长不出来。譬如,在公元1000年时,中国宋朝与西欧相比,经济处于遥遥领先地位,雇佣劳动,工场手工业和商业,还有城市与对外贸易等都已大规模发展起来了。而当时的西欧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生活和国际贸易已不复存在。再稍后一些,到了元朝,从威尼斯来的马可·;波罗见到北京、杭州等城市也是惊为天堂,但是,已经有了那么强大的资本主义“萌芽”了,又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反而在没有“萌芽”的欧洲发展起来呢?
罗水泊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很有道理!它实际上也一直徘徊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水泊先生的进一步看法又是怎样呢?
水泊后来又重新研究欧洲历史,写出的两本书《古希腊札记》和《罗马帝国文化与基督教》都是探讨这些问题的。他以为,世界上有两大文明体系。西方文明是由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文化和基督教思想汇集而成的。例如,古希腊城邦抛弃了“万民之王”的最高政治权威,采取同盟的形态处理各邦关系,内部发展法制、民主政制,确立了公民权利观念,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的佘地,文化得以独立发展,古希腊文明创造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雏形。另外,雅典的民主思想,也是随其海上权力一同兴起的。以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海外贸易获得的巨大利益,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这样,西方文明在吸收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很快超过了东方。
对的,以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有启蒙运动都是从古希腊文明的源头开始的。
水泊的那两本书你可以看看,他还介绍了罗马帝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明形成的贡献。在《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一书中,他又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是东方文化的主要潮流之一。水泊称其为“道统文化”或“皇权文化”,一针见血说:“就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它的主干就是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化,其核心是宗法和封建社会的“礼法”,以其强大力量支配社会,甚至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它另一特点是阻滞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其陷入破坏—;—;修复—;—;破坏的无休止大循环中,就连崇尚传统儒学的梁漱溟先生也哀叹道:“假使中国没有西方文化进来,则再过二千年其生活仍不变。”
罗水泊先生是不是认为,内因是变化的决定因素,应该从中国文化和社会内部去寻找问题的根源?
他对崇祯皇帝感兴趣也是基于此的。他认为,明朝亡于清,肯定不能只怪一两个人,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全面腐败引起的。崇祯皇帝想收拾一下这个混乱局面,但非人力所及。这种社会全面腐败,固然要统治阶级负责,也有我们民族的弱点造成的。水泊对中国传统哲学与社会心理都有零散而精辟的看法,那本笔记也是他读史料搜集到的一些故事,又演绎成了小说形式。顿一下,英夫面容肃然,又看我一眼,水泊认为,任何历史实际上都是一部当代史!
细雨飘下,吴伟业的脸上湿漉漉的。街市上,人们都有一种茫然的急匆匆模样,或是披起了蓑衣,或是戴起了竹斗笠,或是举起了油布伞。当街的那些摊贩们,也纷纷收起摊子四散走开。灰色苍穹真像要硬压下来,挤碎地上的茅屋和瓦房,显得特沉重,空气里散发着一种淡淡的霉味儿土腥味儿。
吴伟业仍然缓慢背着手踱步走,跟在他后面的仆人吴福却有些吃不住劲儿了,他唤了吴伟业一声:
“老爷……下雨啦。”
“哦。”
“我们先回万寿宫吧。”
“不,我们还是去湖边。”
“老爷,我们没有带伞,要是淋了雨怎么办?”吴福有些着急,“我不要紧,就怕您,您的身子骨……”
吴伟业仰起头,望一眼灰蒙蒙的天空,有些百无聊赖的感觉,他只想漫无目的在雨中走一走。“不要紧的。”。他只简单回复一句,仍然往前走。雨未下大,飘飘洒洒几个点子,像是顽皮孩子用手指弹过来的几滴水珠,落在吴伟业的脸上,身上,清爽爽的,又仿佛有一种陌生感。
他很喜欢这雨。在他的诗里,曾经多少次描写了绵绵淫雨中的苦闷心境。滴滴嗒嗒的雨点声,终于使他胸内凄凉与悲哀的情绪得以散发,冰冷的雨点真好像落到了心里。
回过头,他才发现吴福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吴传业有些气恼了。他想,这家伙是不是跑到哪里去避雨了?转念一想,吴福是绝对不会弃下主人不顾,自己跑去避雨!那么,他去哪儿了?吴伟业正举目四下索寻之际,却见吴福气喘吁吁提着两个大斗笠来了,“老爷!老—;—;爷!我在旁边铺店买来的,您戴上吧。”
“好,好啊!”吴伟业拿过这大斗笠,很好玩地翻来覆去看着,又把它戴在头顶上。这顶大斗笠压在头上沉甸甸的,他觉得有些不太舒服。取下斗笠,他抹了一把湿呼呼的光头皮,心里又起了一阵阴云,记得那天朝廷下了薙;发令,清兵押着剃头匠到各家各户强迫薙;发,他正在书房里,忽然妻子郁氏领着一家子人推门闯进来,妻子郁氏噗嗵一声领头跪下,家人跪下一片。他大惊,忙去搀妻子起身:“怎么着?怎么着?这是怎么着?”
妻子双目一合,流下两行热泪:“夫君,薙;发是不得已的事……”
他明白了。其实,这也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妻子还是没有看明白他呀,他若是有心殉明朝故主,早已死了不知多少回了!又何必苟延至今呢。他苦笑一下,什么也不想说。只是向吴福挥了挥手,示意让他请那个剃头匠进来。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