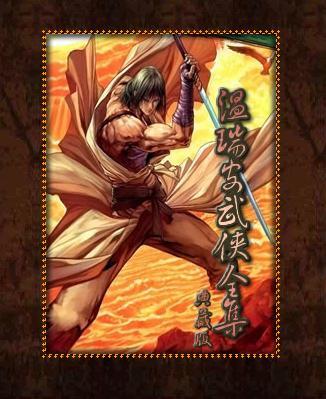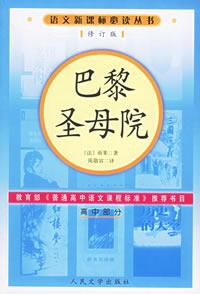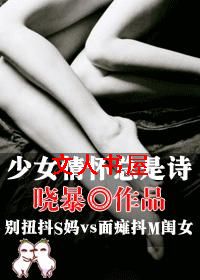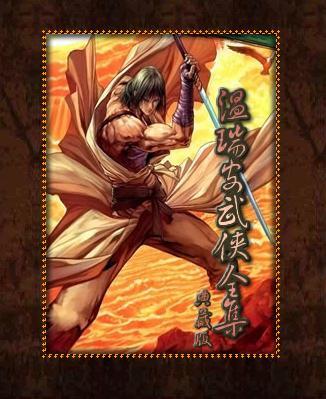情怀巴黎-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奖的保罗·杜卡而故意如此作为。“这个结果,对于杜卡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只是对评委来说,造成这样的结果反而可耻!”保罗·杜卡对于这一事件,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在学习方面,古诺没给我任何建议和意见;相反,与他意见相左的圣桑却是一直坚持支持我,始终为我辩护。”因古诺的势力范围较大,音乐组四评委最终的决议,致使罗马大奖的音乐奖最后“流产”。此次罗马大奖评委不公正的待遇,使性格刚强的杜卡愤然离开了巴黎音乐学院,尽管他还很年轻,并且还有机会继续参加罗马大奖的比赛,但他还是毅然决然放弃了学业。保罗·杜卡多年后不无感慨的说:“不愿意再就读这所让我失望的音乐学院。”
保罗·杜卡经过一段沉静后,选择了一条使人出人意料道路。他决定投身一个与音乐毫无关系的行业—当兵入伍。这也许是让他摆脱学院思想束缚的最有力的举动。或许保罗·杜卡那时觉得这个职业与音乐无关,能迫使自己忘却过去的痛苦,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事实证明,当兵入伍的保罗·杜卡每天坚持锻炼、军训和操练。总之,改经易辙的保罗·杜卡喜欢和大自然接触,可能是这种心灵与自然的交融,使保罗·杜卡的内心萌发了对大自然的深深地爱恋,以后成为著名印象派作曲家的源头吧。
保罗·杜卡在当兵期间,通过与大自然的长期相融,使他有机会思考今后音乐的发展方向。他当兵役期满,再回到城市当中,便开始静下心绪,把内心对大自然的感触用音乐记录下来,并且静心研究历代音乐名家的作品,为今后的音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保罗·杜卡第一部作品在巴黎公演,获得了法国观众和音乐界的好评。作曲家圣桑专门给保罗·杜卡发出邀请,提出同他合作一部歌剧,那是一部杜卡的老师吉罗未完成的作品,保罗·杜卡负责写歌剧的前半部分,圣桑则完成了第四和第五幕的配器。保罗·杜卡与圣桑的合作相当得顺利,他们两人的心情都很愉快,这使保罗·杜卡由此对将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1897年的5月,保罗·杜卡创作的交响谐谑曲《小巫师》在他亲自指挥下在巴黎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原来几乎“十年寒窗无人问”的保罗·杜卡在“一夜成名天下知”,奠定了他在欧洲音乐界的地位,继而成为了法国音乐界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
保罗·杜卡的交响谐谑曲《小巫师》之所以能够成功,我们现在看来,有他的历史原因。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音乐界暮气沉沉,虽然德彪西《牧神午后》的首演,像一道灼亮的闪电,刺破了暮色的尘埃,但也只是显露出了一丝明亮的希望之光而已,这道亮光继而又被沉沉暮色所淹没。巴黎的观众更多地沉浸在瓦格纳的音乐带来的绚丽旋律和装饰奢华的大歌剧表演的氛围当中。法国的音乐评论界此时已分为两大阵营:一派保守,一派是革新,双方经常炮火齐鸣,交锋不断。德彪西成名作《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的上演,也是在保罗·杜卡的成名作《小巫师》首演四年之后。所以我们不难想象,这时保罗·杜卡的处境有多么孤单寂廖。《小巫师》的创作开一代风气之先,它的故事情节精巧,剧情幽默,技术精湛,笔调诙谐。《小巫师》作品是根据古代埃及的神话故事改编而成。是说一个老巫师的徒弟小巫师,在师父那儿里偷偷学到了一句咒语,这句咒语能使扫帚变活。小巫师念起咒语,让它打水,扫帚取水不止,小巫师还没学到停止打水的咒语,眼看屋里泛滥成灾,师傅及时赶来口念解语,才化解了这一场无妄之灾。《小巫师》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幽默的旋律,像一缕清新的春风,吹入到混沌沉闷的法国乐坛。保罗·杜卡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和卓越的音乐才能,逐步奠定了他在法国音乐界的地位。保罗·杜卡虽然饱偿孤寂,但在一步步脚踏实地奋进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后,保罗·杜卡开始涉及音乐评论和艺术研究的领域。保罗·杜卡说:“一个好的音乐家不能只局限于音乐范畴,他必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应该在更宽阔的领域里去研究探索。”德彪西这样评价保罗·杜卡:“保罗·杜卡是自己情感的主人,他有意逃开成功后事物的嘈杂,他也决不允许自己做多余重复的继续,因为太多的优秀的东西放在一起,反倒显得暗淡了,所以他便独自另辟蹊径。”
保罗·杜卡在从事多种艺术研究和探索的开拓之路的同时,他先对音乐前辈大师,如巴赫、拉莫、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韦伯、伯辽兹等人的众多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对前人的时代性、对他们在当时音乐界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后人的影响方面都作了理论性的定义。保罗·杜卡还在欧洲权威性的艺术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当时最有影响的《周刊》、《美术报》、《艺术与收藏》等权威刊物,都曾邀他撰写的艺评文章。保罗·杜卡丰富的学识不仅在音乐界,而且在欧洲艺术界极为罕见,至今无人能企及。
保罗·杜卡著有几十种专著,他在法国及欧洲艺术界影响深远。他所撰写的著作有《音符与音乐》、《戏剧与交响乐》、《音乐和文学》、《音乐和戏剧》、《新诗》、《音乐与创新》、《诗歌与剧本》等等。保罗·杜卡同学们谈到他的评论时这样说:“他(保罗·杜卡)的论述那么独到、犀利而且简明扼要,真使我们惊讶,他的博学和才华,又使我们自愧弗如。”所以后人说,保罗·杜卡只在音乐领域的研究,便完全可以与瓦格纳和伯辽兹的同类音乐成就相提并论。
1905年,著名作曲家福列担任了巴黎音乐学院的院长,事情是因为拉威尔数次未得罗马大奖又引起了世人公愤,当时的巴黎音乐学院院长泰奥多尔·杜布瓦引咎辞职,由福列来接替,福列以开拓进取的风格而著称,他尤其致力于音乐教学和师资的改革,其中教师改革内容之一就是使学院的老师年轻化。杜卡于是接受了他的邀请,虽然保罗·杜卡那时也已经45岁,已不算年轻了,但是以保罗·杜卡音乐方面的成就,比起音乐学院的那些‘古董’,要干练和年轻许多。保罗·杜卡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出色的评论家和博识的学者,他同样也是一位道德高尚,受人爱戴的优秀教师。保罗·杜卡在巴黎音乐学院时期作为全法音乐学院的督学,指导完善了法国各省的音乐学院音乐发展的方向和体制。那时这一职位只有威望极高的人才能担任,督学的权力非常之大,保罗·杜卡利用此权利甚至打破了当时法国音乐界的禁忌。他实行把省属音乐学院的、有才华的老师直接推荐进巴黎音乐学院教书的政策,后来经推保罗·杜卡推荐调至音乐学院任教的老师的人品和才华普遍被师生们认可。
保罗·杜卡学识渊博,他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使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倾倒,他身边经常聚集着大量的门徒。作为教育家的保罗·杜卡不仅独具慧眼,而且还是一位和蔼的长者。保罗·杜卡在教育上特别注重发展学生们的艺术个性,培养学生们形成自己的艺术审美观,包括他们的判断力和鉴赏力。保罗·杜卡曾经说:“年轻人的坦率真诚和执著的信念是难能可贵的,我还没有那么狭隘,不允许学生们去探索。”他经常鼓励学生们:“要有理由坚持己见,在探询真理的道路上,从那些点点滴滴当中去追求真理,不可放弃。”保罗·杜卡高尚的品德,虚怀若谷的情操以及为人师表的风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们的人生观。1934年,法国政府决定提名他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法兰西艺术院在艺术界享有盛誉,该院的院士资格为终身制,只有原院士谢世,才由评审组经过严格的审查,指定新的成员接替,法兰西艺术院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机构之一 。这是保罗·杜卡一生唯一的一项官方荣誉。
1935年,保罗·杜卡重病缠身,但他仍在给学生们继续上课,他的病情连他的最好朋友都不知道。身染重病的保罗·杜卡一再对别人说:“我离终点还远着呢!”1935年5月17号夜晚,他给学生们上完课,感到心脏不适,当天夜里便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学院的同仁和学生们对他的离去异常悲痛。保罗·杜卡的挚友音乐家罗伯特·布尔塞尔这样评价:“ 保罗·杜卡一定知道,他的离去,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遗憾。保罗·杜卡虽然悄悄地走了,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如果这句话用我们中国语言来形容,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时光流逝,光阴荏苒,七十年岁月悠悠飘逝。保罗·杜卡是否还记得在他众多的门徒当中,有这样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他贫困得几乎靠乞讨生活,他的穿戴寒酸,他进考场以至门卫把他当作乞丐拒之门外,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坚强的毅力,他满怀赤子的报国之心……他就是我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冼星海曾在巴黎留学自述中这样说:“保罗·杜卡是世界三大音乐家之一,……他不嫌我贫苦……竟肯收我做门生,他给我各种援助,送我衣服,送我钱,不断地鼓励我……并答应准我考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曾仔细地寻查过有关保罗·杜卡的通讯材料,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他们师生有关书面上的通讯记录。我想是因为冼星海在巴黎时生活太贫苦,生活中必需要节省每一份开支的原因吧。
保罗·杜卡是法国音乐界受人敬仰的一代大家,他也为中国培养出了冼星海这样优秀的东方之子,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保罗·杜卡和冼星海是东西方音乐界的两座傲然丰碑,他们的学识和品德,永久地屹立于人类民族艺术之林。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1)
协和广场喷泉见证了格什温的音乐道路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乔治·格什温
题记:七十七年前,美国音乐家格什温到巴黎,观埃菲尔铁塔,游塞纳河畔,品法国红酒,逛香榭丽舍大街,有羡慕、有景仰、也有忐忑不安……
美国现代著名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928年因受纽约交响协会的委托,准备写一部描写美国人到巴黎旅行、感受艺都生活的作品。1928年的3月,他便带着这个计划,与他的弟弟一起来到巴黎采风。
在此之前,格什温曾经来过巴黎两次,每次都因为安排紧张,只能蜻蜓点水似的一带而过。与以前不同,这次他有足够的时间感受花都生活的“浪漫之旅”。
他先到巴黎的一个旅馆里住下,经过两天的休整,除尽了旅途的疲劳,开始计划第一站便去埃菲尔铁塔,看看这座居世界第一高度的巍峨建筑的容貌。从他住的旅馆去埃菲尔铁塔必须要经过荣军院。荣军院建于17世纪,建设之初是太阳王路易十四计划用来安置残疾军人的地方,它却因1840年安葬拿破仑的遗体而扬名与世。埃菲尔铁塔高耸入云,巍峨壮观,像一座俯望着塞纳河的保护神,清纯的河水从它的脚下流过,波光淋漓,姿态万千,巴黎人常说:“埃菲尔铁塔,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让你终生难忘。”格什温踏着绿茵向前走,穿过战神广场。人们说在秋天时广场最美,凌乱的叶子随风洒落,如乡愁一般扫也扫不干净。塞纳河的左岸便是举世闻名的巴黎拉丁区,这里常聚集着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以及画家和诗人们,也有演艺界的名流经常出没,小贩们细长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荡在拉丁区的上空。求知的青年穿梭在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国家科学院周围,有的三三两两信步于卢森堡公园,有的则渐渐隐掩进树荫茂密的小巷里。法国人说,当一个人从喜欢勃艮第转而偏爱波尔多时,标志着他已步入中年,趋于成熟。勃艮第酒浓郁、醇厚,波尔多酒细腻、优雅,人们把左岸比作“勃艮第”,右岸则恰似“波尔多”。
塞纳河水粼波荡漾,手风琴的乐曲悠扬。河水缓流到巴黎的中心,有两座小岛,这便是巴黎最早的发祥地—圣路易岛和西岱岛,巴黎圣母院和无数法国名人的故居就坐落在两个岛上。巴黎圣母院从开始兴建到正式建成,用了200年的时间,拿破仑自封皇帝的加冕仪式便在这里举行。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所描写的外表丑陋而内心善良的阿西莫多和吉普赛姑娘埃斯梅拉达感人至深的爱情,也是在巴黎圣母院上演。左面那厚重的建筑,便是路易十五的爱妃玛当·狄帕丽被推往断头台的地方,两个多世纪前的革命烟火已经散尽,但巴黎看守所的高墙门楼依然有些神秘。格什温穿过路易·菲利浦桥,河水荡漾,四周宁静,时光似乎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