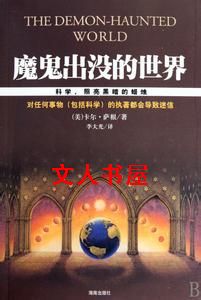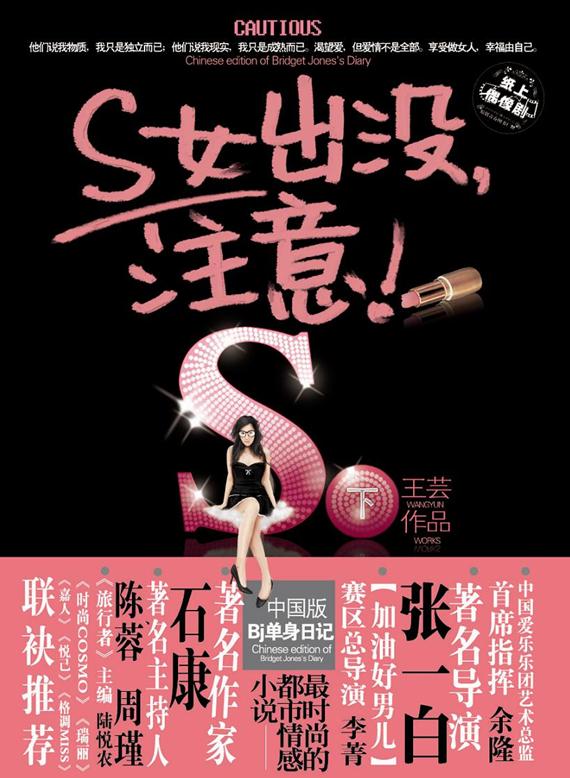鬼魂出没-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特凌结婚十四年来一直参加专业会议,听她杰出的丈夫发言,作为妻子,这一天下午肯定没有为丈夫担心的理由。
在会议厅前面有个讲台,台上坐着五个参加讨论的男科学家,一头银白色金发、戴厚镜片眼镜的诺曼?马特凌在其中显得十分突出。他们正在讨论一个紧急问题。朱丽亚集中注意力倾听:他们讨论的是诸如“曲率的半径”、“超对称性”、“换相”、“地平线”之类的问题。这些都是使朱丽亚感到烦恼、而又熟悉的问题。她的丈夫不是多次向她解释过这些问题吗?——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诺曼?马特凌对此笃信不疑,无论谁落后如果不是悲剧,也是遗憾。
朱丽亚自豪地看到,会议厅里一排一排的男男女女,人人都身体朝前倾,聚精会神地倾听讨论团成员争论最近在实验室所作的试验的重要性。这个试验通过机器加速两束质子,使其速度几乎等于光速,然后让这两束光迎头撞击,在撞击中温度升高到大约能使宇宙中的弱势力量和电磁力结合起来的程度,惊人地模仿了早期宇宙的状况——宇宙的年龄只有百亿分之一秒时的状况。“因此,”诺曼?马特凌声音颤抖着说,“——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论——”
朱丽亚看见诺曼身上穿着一件臃肿、已经磨损了的猎人绿灯芯绒夹克,她肯定这是一件她多年前已经扔掉的衣服。又看见诺曼脑瓜上的头发向上翘,她颓丧地往后一缩。他为什么不用水把头发压下去!诺曼认真起来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从座位上笨拙地站起来,走到黑板旁边,潦草地写了一长串难以辨认的方程式,开始唾沫横飞,结结巴巴地说起来;这时他的样子活像用两条后腿站起来的熊,为了努力保持平衡,眼镜朝里看——然而,讨论团其他成员对他却尊敬有加!大厅内鸦雀无声,人人都津津有味地听着。诺曼在发布宇宙早期换相的理论,这一换相是紧接着宇宙大爆炸发生的,对以数学以外的方式得到的理解提出了挑战:10…35秒(用小数点后34个零和一个1代表)。在这以前夸克显然冻成了强子。
朱丽亚不安地微笑了。她过去知道这个理论吗?
所谓换相指的是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例如从气体变成液体,从液体变成固体,又从固体变成气体,从表面上的整体变成无数碎片。换相不是可以推论出来的,而只能靠从经验中获取。换相既是不可取消的又是可以取消的。
诺曼?马特凌谈的是超对称粒子,把观察到的世界组成一个镜子里的形象;由此人们可以演绎出一个影子宇宙,一个我们居住的镜子里的宇宙——“与我们的宇宙互相影响,”诺曼激动地说,“只通过地心引力。因此——”说到这里,讨论团里另一名科学家,卡尔技术中心的天体物理学家,粗鲁地打断诺曼,大步流星走到黑板前,把自己的方程式写到黑板上。他的方程式也令人看得莫名其妙。
尽管她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似乎接近了意识不到的危机,两位科学家交换的意见,还是深深吸引了朱丽亚。她悄悄离开座位,去找厕所。
她多次参加过中心的会议和社交聚会,然而令她感到沮丧的是,每次找女厕都要费一番工夫(也许在这个男人占绝对优势、修道院似的地方,女人用的设施本来就少)。那一条条走廊、一段段楼梯,一道道朝向空荡荡的日式花园的死胡同构成的迷宫——除了使她想起飞速扩张的宇宙现象,还能想起什么东西?模糊意味着遥远。还有疯狂。
但是朱丽亚顾不得想这些东西。她紧紧抓住手提包的指关节都发白了,她只顾得想肠子里的不舒服。
接下来——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中心厨房拐角处她找到了女厕所。
她如厕后站在洗手盆边,把凉水泼洒到脸上。在旁边的洗手盆前面站着一个胖女人,她相貌平平,灰白的头发编成辫子,缠在头上。她在使劲地洗手。朱丽亚一边擦脸,一边强作轻松愉快地说:“但愿我听得懂他们说的话,你说是吗?我知道他们掌握了宇宙的秘密——真正的宇宙,不是我们这个宇宙。其实,在中学的时候我的物理和微积分的成绩都是A,我不是一个一窍不通的人,但是我现在把学过的东西全忘了。而且越来越糟。什么是‘夸克’,什么是‘黑洞’,‘欧米加’代表什么东西,这些问题跟我说了几十遍——可我就是记不得。我永远学不会。有时候我但愿这些东西全都走得远远的!干脆——消失!”朱丽亚笑起来,她以为那个女人也会跟着她笑;但那个女人只是冷冷地瞪了她一眼,在毛巾上擦干手就走了。朱丽亚过后才想起,那个女人不是别人,而是艾尔萨?黑森博格,是大名鼎鼎的维纳?黑森博格的亲戚。而维纳?黑森博格则是帕洛马山天文观察站著名的天文学家。她感到大跌眼镜。
朱丽亚望着洗脸盆上自己模糊的映像:“你真是个笨蛋,居然把她当作你自己!”
朱丽亚不愿意错过学术研讨会的下半部分。可是在回大厅的路上显然由于匆忙,拐错了弯。她发觉自己走进了一条气闷、太热的走廊,拐了一个弯,来到中心的厨房区后部。这里有几个身强体壮、系着白围裙的年轻黑人,闲散地围着一张桌子抽烟(抽大麻?还是哈吸吸①?朱丽亚的鼻孔里钻进了一股辛辣、刺鼻的气味)。黑人们见到朱丽亚,眼睛瞪得老大,显然全身都麻木了。
朱丽亚羞涩地说道:“对不起——看来我迷路了,我怎样才能回到会议厅呢?”
换相(3)
那些男人还不停地盯着她,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的人。他们此时立正似的站了起来。最年轻的一个,瘦长个子,棕色皮肤,理了一个古怪的平顶,在接近颈脖的地方留了一圈毛发,他刺耳地咯咯笑着把烟藏到了身后。另一个皮肤紫黑的矮胖子,脖子粗,脸盘宽,满脸凶残,嘴唇看起来有点儿肿胀,朝朱丽亚咧开嘴,不怀好意地笑着。
他们认识我吗?我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不是在等我,此时此地,这么凑巧?
一共有四个黑人,都穿着白得耀眼的侍者工作服。雪白的牙齿,白森森的笑容。白森森的笑容里还夹杂着金光。那个最年轻的黑人左耳朵上戴着几个金耳环……如果这些耳环是个代号,那么,它们代表什么意思?朱丽亚看见这几个男人在交换眼色,狡猾而灵活地朝前挪。其中一个身高不下六英尺七英寸,皮肤黑得像黑檀木一样闪闪发亮的男人敏捷地闪到她的右边,挡住了她的退路,使她无法逃脱。
朱丽亚双手紧紧地抓住手提包。她挺直腰杆站着,尽最大的可能保持威严。她吓坏了,全身瘫软,但极力平静理智地说:“我——我看来拐错了弯。你们能帮助我吗?请你们帮帮忙。哪一条路是通往——”她住了口,不知道这些粗俗的黑人听不听得懂“圆厅”这个词,“——大厅的路?大楼的前面?”黑人们的眼睛瞪得更大,闪闪发亮,笑得嘴也歪了。“我在参加研讨宇宙构造的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我的丈夫就是参加研讨会的一员,因此我不想落下一个字。他们在揭开宇宙的奥秘!人类对天体的概念正在经历彻头彻尾的大变革!因此,如果你们能帮助我找到回去的路,请——”黑人们像食肉的黑猫,脚下十分轻巧地朝她逼近,朱丽亚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
朱丽亚突然惊慌失措,转身就跑,扭着了脚踝,差点跌倒,手提包飞了出去。最年轻的黑人抓住了她,他的手指头像钢铁一样坚硬,长得足以箍住她的腰肢。“不!求你们别这样!放我走!噢,求你们啦!”她乞求道,“我从来不歧视黑人,我发誓!我知道昆斯顿是白人的天下——但我没有——邻里之间的偏见!我丈夫是——”那个年轻的黑人尖声怪笑,把朱丽亚蛮横地推给他的一个同伙,这个同伙抓住朱丽亚的上臂,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狠狠地一扭。朱丽亚用力吸了一口气,想要大声叫喊,但是做不到。她低声下气喘着粗气喃喃说道:“我的丈夫是——”
可是她头脑里一片空白。她记不起丈夫的名字,连她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不在,如果在?——我是谁?
朱丽亚?马特凌勇敢地和袭击她的人搏斗,尽管他们人多势众,而她又是个吓坏了的细弱女人,她准知道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她叫不出声来,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叫喊——别!别!求你们别!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讨厌的嘴唇粗野地在她的嘴唇上磨擦,一巴掌打得她耳朵嗡嗡地响。她的乳防被抚摸、被挤压、被抓捏;屁股像揉白面一样被揉搓。不要,求你们不要对我动粗,不要在这里动粗!那几个男人高高在上,对她奸笑,发出一股原始的男人的汗臭——令人毛骨悚然!朱丽亚被他们推来搡去,从一个男人推到另一个男人,仿佛她是个猎物,或者是个活的篮球、足球——这边挨一掌,那边挨一拳,不管她怎么哭着哀求:不!不要!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那几个穿着白得耀眼的侍者服的黑人对朱丽亚?马特凌毫不怜悯。
就在这座大楼里,她杰出的丈夫正在高谈阔论宇宙的结构,探索宇宙的来龙去脉,而朱丽亚?马特凌的手腕却像被紧紧地铐上了钢铁的镣铐,项背也被勒住,她被拖进热气腾腾的厨房,像牛羊肉一样被灵巧的手小心地端到桌子上,与此同时黑手迅速地挪开果盘、色拉(研讨会后为参加会议的两百人准备的宴会马上开始);此时朱丽亚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救命!不要!求求你们!她的蓝色斜纹套裙被猛然撩起,裤衩被扯下来,手指戳进了隐私部位,周围都是狞笑的黑人,哼哼哈哈地尖声叫喊啊—嚯!哈!白×!咦!哇!朱丽亚头昏眼花只见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滴到油毛地毡制成的砖面上,她是不是有一颗牙齿松了?不要!不要!可怜可怜我吧!求求你们!可是他们毫不怜惜朱丽亚?马特凌,他们的手此刻放在朱丽亚一丝不挂的身上,把她紧紧按在桌面上,其中有一个骑在她的身体上,黑黝黝、因充血而肿胀起来的巨大的荫。经,像手提钻一样热辣辣地从毫无遮挡的屁股沟狠狠地、毫不留情地戳进肛门,戳进了女人柔嫩的体内,那地方从来没有被男人碰过,那个她忘了名字的丈夫更是肯定没有碰过——好一阵钻心的疼痛!
此时朱丽亚?马特凌终于吸了一口气喊出声来了,她喊呀,喊呀。
醒了。又一次躺在床上,躺在黑暗中,躺在乱七八糟、一股汗臭的被单里。
这么说,我不在,如果在——我是谁?
多么可耻。难于启齿。
朱丽亚对这个梦十分反感——那么栩栩如生,是在做梦吗?——把它忘了是对她最佳的办法。然而,第二天,第三天,虽然梦中的细节迅速地淡忘,恐惧感却挥之不去——似乎,不知怎的,这恐惧感始终存在于宇宙的另一个维度。
当然,朱丽亚决心在诺曼面前掩盖心中的狂躁,如果让诺曼知道,他会感到困惑不安。人心中狂躁,而能不发疯吗?朱丽亚心中纳闷,不知道人的狂躁是否能像那些她老记不住名字的亚原子的粒子一样穿过固体——是尾中子?还是微中子?——夹带着混乱,却又在观察得到的世界上激不起涟漪。
他永远不会知道。他会知道吗?
朱丽亚不记得细节了,也不记得梦的轮廓(只知道梦中的情景是发生在中心,这个地方是最不适合做噩梦的地点)。朱丽亚怀着女人的羞愧,内疚地意识到,她又一次给了一个或几个男人致命的影响。
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男人,只要动了她,就会消失。
她莞尔一笑。不,她不是笑——而是忧虑、不安。
我是“克”男人的女人吗?能下意识地置他们于死地?
换相(4)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荒唐的,纯粹是胡思乱想;然而,一天天、一夜夜地过去,她害怕睡觉,害怕黑夜对她施加的魔力。诺曼竟然没有看出蛛丝马迹——实在太幸运了!朱丽亚拼命保护他,像母亲保护有天才但患有隐性残疾的孩子一样。朱丽亚吻他的时候,迎接他的时候,或者在他即将离家,真像小孩儿一样惊喜地微笑着拥抱她的时候,她心里总是说:他永远不会知道。必须永远不让他知道。
朱丽亚同样下定了决心,无论多么恐怖,她必须不去想它,也不能影响她在昆斯顿艺术馆的工作。她毕竟是个职业妇女:难道不是吗?
然而,使朱丽亚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情形到底还是发生了。即使是在艺术馆,在办公室的避难所里,无处不在的预感和害怕也来骚扰她。我究


![[综]有村民出没请小心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7/715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