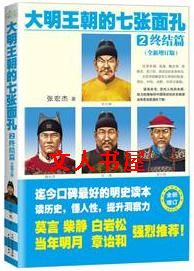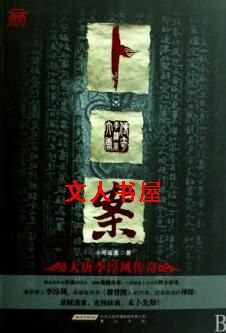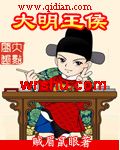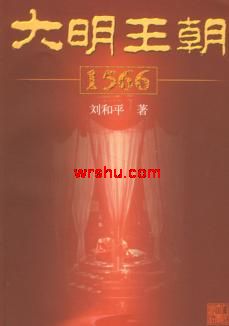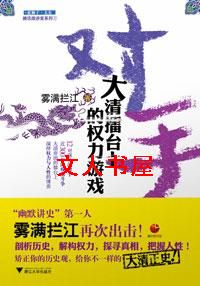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隔了一个月,十二月中,嘉靖两次试探。第一次,只提出单给蒋氏的兴献后称号加尊皇字,被杨廷和顶了回去;第二次,御批于兴献帝后尊号上“各加一皇字”,又被拒绝。由这两次行动,可以看出嘉靖背后蒋氏的作用,因为第一次单提出给兴献后加尊皇字,可想见这女人特别在意,也闹得特别起劲,被回绝后,羞恼之下索性提出两个一道加。杨廷和不胜纠缠,表示不能受命,自己唯有引退。表示一出,即有百余官员齐声高叫“老九不能走”,上疏皇帝务加挽留。嘉靖一见,做了个顺水人情,“优诏留之”{30}———他本来意在试探,除了试探杨廷和现在态度究竟怎样、反对有多坚决,也想试探杨在朝中受拥护程度如何。现在,这两点他都已清楚。看来,事情暂不能操之过急。
他需要时间,来搬走杨廷和这块大石头。
不光是嘉靖需要时间,别人同样需要时间———那些希意干进、却还拿不定主意的人。时间将为他们把窥伺之门推得更开一些。不过,开头总免不了有几个去充当替罪羊。
例如一个叫史道的兵科给事中。此人自以为已看出端倪:皇帝与首辅势不两立,杨廷和这棵大树迟早要倒———这一点,他的确搞对了。他不曾搞对的是,跳出来充当弹劾杨廷和的第一人,势必会成为嘉靖倒杨行动的祭品。
他上疏质问,正德年间朱厚照荒诞不经地自称“威武大将军”,没有听说杨廷和有所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31}他说得有道理,但一是持论过苛,难以服众———像武宗那样不可理喻之人,力争又有何用?二来,这番高论其实有犯忌之处,嘉靖看了未必舒服,因为他将兴献王尊号问题与朱厚照为自己胡乱加“镇国公”、“大将军”、“总兵官”头衔相提并论,岂不是嘲笑嘉靖昏乱。三来,他跳出来弹劾杨廷和,是很好的,不过嘉靖却不宜立刻倒屣相迎,相反他一定要表现得很生气,挺身回护廷和,这才便于他将来除掉廷和时得以阐明如下姿态:大家看啊,朕都保护他N次了,实是迫不得已的。所以,史道成为倒霉蛋儿,一道谕旨,他被送入诏狱,而杨廷和因遭弹劾依例提出的退休申请,却不被批准。
紧接着,又一个冤大头跳将出来。御史曹嘉替史道打抱不平,他认为史道弹劾杨廷和,尽其职责,没什么不对;皇帝把史道下诏狱,对廷和则温旨慰留,处置有失公道;又暗指替廷和及为之辩护的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这个指责很严重,大臣要公忠体国,聚为朋党实为大忌。所以曹嘉此言一出,马上引来轩然大波。众臣反应显然是协调一致的,从曹嘉上疏第三天起,连续十一天,内阁成员集体留在家中,没有赴阁办事。而后,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位大学士,以及刑部尚书林俊、兵部尚书彭泽、户部尚书孙交、吏部尚书乔宇,各自提出辞呈,杨廷和和蒋冕连续递交了几次。嘉靖概不批准,三番五次派员至上述诸大臣府第传旨,请他们回阁视事,杨廷和等却称疾坚不出。表面看来,嘉靖仁至义尽,杨廷和们却颇为托大,乃至有要挟之意。其实,曹嘉的说法确实让人吃不消,廷和等人必须讨个说法,在未得到明确说法之前,不可以稀里糊涂地出来工作。而在这十一天里,嘉靖虽对杨廷和们好言相慰,一再重复如何寄予信任,却始终回避曹嘉劾章中的关键之处,即这些重臣之间是否存在朋党关系。以嘉靖这种聪明绝顶之人,早该清楚杨廷和避而不出所为何来;但他偏偏言不及义,尽说一些空洞的劝慰的话,且言语间不时微指杨廷和们只爱惜自己名誉,置大臣之义于不顾。似乎,他有意延长内阁瘫痪的时间,来彰显杨廷和等人的自私负气。直到后来,十三道御史刘廷簠在奏章里点破这一点,“自古去大臣者,以朋党为说”。并举出正德初年刘健、谢迁、韩文被以朋党之名搞掉的例子,嘉靖这才表示:“朝廷清明,岂可辄以朋党之说指斥大臣。”至此,十多天内阁空不见人的局面方告结束。杨廷和们虽然得到了“说法”,但这么多天“擅离职守”或“旷工”,纵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究竟也造成不好的影响,而在道德上付出代价。至于那个曹嘉,在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之后,只落得一个贬谪的下场。唯一的赢家,是皇帝本人。{32}
嘉靖:万岁,陛下(13)
这时,是嘉靖二年正月。
转眼来到年底。万岁小爷入住紫禁城已然两载,眼看就要十八岁。若在现代,十八岁即为成人,从此取得公民权。明代无此一说,但十八岁仍不失为人生一个重大关节,乳臭未干的嘉靖,目下应该喉结突出,颔生黑须,昂然一丈夫了,也终于到梳理羽毛,振翅高飞的时刻。
是年,对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及浙江来说非常不利,先是大旱,后又大涝。南京户部右侍郎席书递交的报告称,该地人民景况只有三等:“有绝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贫难已甚、可营一食者;有秋禾全无、尚能举贷者。”{33}就是说,处境最好的也需要告贷维持。
恰在此情势之下,嘉靖拟派遣内官前往南方办理织造。所谓织造,指宫中帝后等人服饰的供给,其本身费用已属奢巨,加之任事的内官往往乘机大捞,扰民极重,正常年景已令地方不堪,何况又逢大灾之年。所以消息传出,朝臣纷纷上疏谏阻。但嘉靖却如吃了秤砣一般,铁心不变,一再催促内阁拟旨。杨廷和反复申明江南民不聊生,人民犹处水深火热之中,如逼煎太甚,“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嘉靖就是不听,君臣再起争执。前者见无法说服内阁拟旨,竟撇开内阁,直接让人(应该是某位近侍)草诏,并付诸执行。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公然的排斥。正如杨廷和所说,根据祖制,明朝“诸所批答,俱由内阁拟进”,这是制度,在当时犹如法律,而嘉靖的做法不啻于越过法定程序,性质非常严重。
杨廷和震惊于嘉靖的一意孤行,忍不住质问道:“今臣等言之不听,九卿言之不听,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独二三奸佞【指宦官】之言,听之不疑。陛下独能二三奸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
末一句深中肯綮,语气未免过重。老首辅忧民心切,激于义愤,一时不能自已,而说出这种近乎顶撞的话来。
其实,嘉靖是用这种举动,宣布对杨廷和内阁的遗弃。杨廷和感觉到了这一点,却又难以置信。他在奏疏中提到一句:“臣等固当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则止之义。”这并非正式辞职,而是希望借这样一句话,换来皇帝积极的自我纠谬的回应。
但此番较量相较以往,判然有别。一贯对杨廷和加以挽留的嘉靖,突然改弦更张。《明史》记载,杨廷和于嘉靖三年一月退休,“帝听之去”,并无片语劝留。这就好像一出戏,推来阻去的一直很热闹,可突然间,一切就戛然而止了,人声鼎沸的世界瞬时死一般寂静,以至于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
自正德崩后,一手敉定政局、定策迎立、拨乱反正、宵衣旰食、勤勤恳恳的老首辅,就这样去了。类似杨廷和这种级别的重臣,如果提出辞职,通常的做法是前两次都要予以拒绝,以示挽留,第三次才予批准———哪怕皇帝已极讨厌该人,巴不得他滚蛋,也要做做这种表面文章。嘉靖不按规矩出牌,尽管杨廷和久有去意,乞休并非假心,但从皇帝方面来说,至三方准,其意不在挽留,而是以示对一个服务多年、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臣的尊敬,嘉靖却冷酷地剥夺了这种敬意,尤其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出手如此辛辣果断,充分展示了他意志坚定、恩威莫测的性格。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还将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一点。
杨廷和走了,不因“大礼议”,而因织造,这总让人感到蹊跷。在大礼问题上,杨那样执拗地与嘉靖作梗,而且多次恳切请辞,嘉靖竟一概不允。他不倒于“大礼议”,却倒于不相干的事情上,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明眼人自能看出,嘉靖此计乃借刀杀人。因为“大礼议”本身未见分晓,尚无结论,不可能以此斥退廷和,那么很好,我就利用织造之争把你挤走。织造这件事,有很多刻意而为的迹象。江南灾情那样严重,嘉靖偏偏要在此时行此事,且当从内阁到各部负责人再到科道官等所有人一致反对的局面下,不管不顾,矢志以行,甚至不惜采取撇开内阁、直接拟旨的极反常的举动……这一切,结果势必要将杨廷和推到风口浪尖,并迫使他以辞职来尽最后谏劝之责的地步。这太像一个精心构设的圈套。
嘉靖:万岁,陛下(14)
嘉靖三年一月,朱厚熜以这样一个行动,宣告杨廷和柄国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此后自己长达四十年真正“独立自主”的专制统治的开始。
此时此刻,他必定深深怀念着张璁。
自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兴献帝后称号以妥协方式解决,暂告一段落以后,张璁就被杨廷和调离北京,他得到了南京刑部主事的任命。杨廷和以为,让此人远离京师,减少他和皇帝接触的机会,庶可少生事端。
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张璁之去南京,恰好促成了继统派阵营的形成。先前在北京,张璁独力支撑,孤掌难鸣,几乎没有市场,任他怎么折腾,只怕也难成大事。在理学观点上,当时南北两京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是正统派天下,一个是新潮派渊薮。因此到南京后,张璁意外邂逅了一批同志,一个叫桂萼,一个叫方献夫,一个叫席书,一个叫霍韬。这几个人同气相求,同忧相救,交往日密,一起就议礼问题充分切磋,遂结成统一战线。
仿佛掐准了似的,杨廷和这只“拦路虎”离去的当月,一道来自南京的重提议礼问题的本章也送达御前。作者是南京刑部主事桂萼,题为《正大礼疏》,明确提出,“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即蒋氏】曰圣母”{34}。
三年前,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大礼议”首回合,嘉靖如愿以偿给自己父母加尊帝后称号,但同时也以承认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亦即礼法上的父母———作为交换。眼下,桂萼做的就是这个翻案文章。
它来得正是时候,嘉靖得疏大喜,即批转廷臣讨论。此时,原“大礼议”反对派领袖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均已去职,蒋冕接首辅之位,九卿及各部侍郎以上人物,多数仍为杨内阁时代旧人,北京的政治气候仍对嘉靖不利。
桂萼疏文下到礼部,现任尚书汪俊召集七十三位廷臣进行讨论。当年议尊号时,汪俊即与毛澄同一立场“力争”,这次也不出意料,由他汇总的廷议,明确反对桂萼的主张;同时还特别指出:“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35}这应当是事实,汪俊不敢瞎编: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种观点的总共四人,而反对者达二百五十余人,完全不成比例。
没有关系,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准备。他一面对内阁和礼部施压,一面征召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来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从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对派节节败退的一段时光。由于杨廷和这唯一堪称德高望重的枢臣引退,反对派思想虽仍然统一,但却少了中流砥柱,根本无法制约皇帝。他们先是同意兴献帝后称号中增加原先杨廷和执意不从的那个“皇”字,然后被迫接受兴献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样。嘉靖却得寸进尺,又提出在皇宫内为父亲设立牌位以便奉祀。
事至此,反对派明白,皇帝陛下必尽伸其志而后已,然以职责所在,他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纵然是螳臂,也须挡一挡车轮,求个心安理得而已。
于是,在设兴献神主的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汪俊等人,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坚决抗旨。这类似于弈局败势已定的情况下,刻意弈出错招,来替自己找个台阶。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轻、藐视纲常。得此重责,汪俊和首辅蒋冕旋即引咎辞职,请求顺利地通过。首辅之位由杨内阁硕果仅存的毛纪接替,而对于“大礼议”至关重要的礼部尚书———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代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权力的变化,总是体现于并通过人事变动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