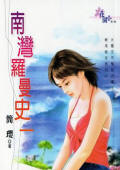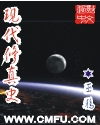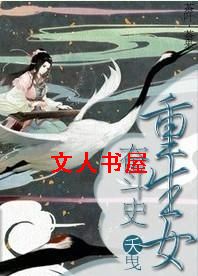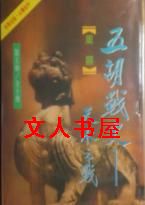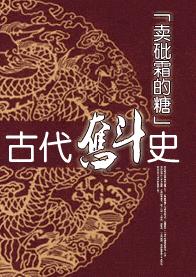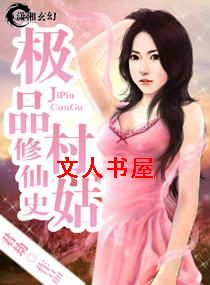中国知青史-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返城风潮(1)
196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城市敲锣打鼓欢送又一批知青下乡或支边的同时,已经有些下乡知青陆续返城了。
(一)参加“大串连”
动荡始于“大串连”。1966年9月5日,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两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革命师生来京,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都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这使串连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和必要的经济保证,标志着“大串连”这个“###”中参与者最广泛、为社会造成震荡最强烈的运动的正式开始。
中央发动这场大串连的最初动机,是想借助这一形势,将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但大火一旦在全国熊熊燃起,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播火者的一厢情愿发展,火苗一下子就窜向了那些中央绝对不想让其燃到的角落。
知青问题就是这样的角落。
串连的参加者很快就从大中学校的师生扩展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刚从学校出来不久,仍带着学生气的知识青年,也是热情的参与者。
最初,他们与在校学生一样,是出于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热情与好奇而投入进去的。毛泽东既然说,每个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知识青年当然也不能例外。最早动起来的是在大城市郊区插队的北京、天津等地知青,他们信息最灵,而且插队不比在农场,少有纪律的约束。他们想到城市去了解究竟。有些离校仅一两年的知青,想回母校去参加“###”,与那些留在学校的同学一道,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除了单纯的革命热情之外,与当地干部社员的矛盾,尤其是与“四清”工作组的矛盾,往往是导致知青起来造反或返城的直接原因。
许多知青最初曾与当地社员或农场职工一道投入到了当地的“###”之中,结果或是触怒了当地的有权有势者,或是因过激行动触怒了当地群众。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有的还渊源有自,矛盾冲突从“四清”就已开始,其中一类情况是,一些知青的处境与自身政治条件较好,于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革命,眼里不揉沙子,不断向当地干部和社员发难,反对“三自一包”,反对“瞒产私分”,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遭致地方干部和社员的反感,有的在“四清”中就与工作组站在一起整过当地干部,也有的被工作组作为新鲜血液、依靠对象,在当地干部被打倒后上台如1965年、1966年两年到上海市郊金山县某大队插队落户的50多名知青中,有的一下乡就担任了政治队长、团总支副书记等职,结果“###”一爆发,就遭到当地群众的批斗。参见《活跃在广阔天地里的一支突击力量》,《文汇报》,1968年9月10日。,“###”开始,被整干部和社员将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他们被逼无奈,只好回城。
也有的地方情况恰恰相反,如我们在上一章谈过的那样,知青因出身不好,早在“四清”时就已被工作组划到阶级队伍之外,“###”爆发后更进而受到当地贫下中农组织“贫协”的排挤。如1965年从北京到内蒙古临河插队的几个女知青说,队里“有人借口我们出身不好,不让贫下中农与我们接近,甚至把知识青年在社会上担任的职务全部取消”。即使有的知青出身并不属于“黑五类”,但他们毕竟是从“修正主义的旧学校”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既然“###”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旧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那么从这种“黑校”、“大染缸”里出来的,当然不会是好人,当然要受贫下中农的管教和批判;再加上前面多次谈到过,有些城市将一些有小偷小摸等毛病的社会青年甚至劳教分子混入知青中一起送下乡,这一切已经导致了知青在农村地位的下降,一逢“###”这种特殊环境,潜在的矛盾便一下子形成冲突,农民对知青的歧视、反感便无所控制地发泄出来了。有些地方一贯将知青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对待,“###”爆发后更是有恃无恐,如湖南零陵地区有个公社在1967年初张贴一份布告,宣称春节期间,凡地富反坏右与上山下乡知青未经允许一律不得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交由贫下中农批斗;广东增城县一个生产大队每召开群众大会,都要宣布知青和“五类分子”一律不得参加;1965年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参加建设的上海知青,到场不久就赶上场里“大抓阶级斗争”,一大批知青竟被农场公然开除回沪。这类纯因政治原因产生的矛盾,与当时整天高喊的与工农结合口号,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尖锐的讽刺。知青在农村既然无法再待下去,又适逢“大串连”这样难得的时机,便纷纷回城去“闹革命”了。
返城风潮(2)
也有的知青并未立即返城,而是在当地扯旗造反,四川合江的插队知青曾这样叙述他们当年的那段经历:
离我们不远的北碚境内,几所大学里都闹起来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的红卫兵在北碚街上撒传单,贴大字报,搞大辩论,搞得不亦乐乎。我们农场有知青去北碚,捡回一些传单传阅后,摩拳擦掌,意欲起来造反了。工作组见此,意欲拉拢部分知青,便急忙刷出大标语: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一面表态支持原来为工作组最卖力的几个知青成立红卫兵,意欲操纵农场的红卫兵组织。但事态不但没照这位湖北佬的意思发展下去,而且连农场里原先那几个工作组的贴心豆瓣——打斗知青和农场当权派(场长和指导员)的打手对工作组也倒戈相向了。工作组见情况不妙,便连夜烧毁材料,摸黑逃下山去……
此时农场知青已迅速成立了一支有好几十人的红卫兵队伍……几天后,在草街地区,以我们知青农场造反团为首,串联当地各工矿单位的造反组织数千人开了大会,成立了草街地区联合造反司令部,我们农场知青刘某任总指挥……之后,知青造反团就离开草街,浩浩荡荡开进县城,参加县里更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去了。时在1966年秋。戴克学:《老知青###读书梦》,《龙门阵》,1993年第4期。
可见造反最初的动机,是与工作组的矛盾,像这类情况在当时是很多的。
还有大批的知青动机更为简单,他们对“###”、对造反并无兴趣,与当地干部也谈不上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不过是借此“千载难逢”的时机,免费乘车回家而已。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那些刚刚下乡不久的知青身上。再说中国的农村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角落,意识形态问题并非在处处都像上述地区那样严重。到甘肃的天津知青回忆说:“(到甘肃后)每天就是开沟、挖大、小渠,平整土地,下过雪也让干活,用镐刨冰土,有些人受不了了,就开始嚷‘回城闹革命’,跑回了家。一开始连里干部还派人去追‘逃兵’,后来干脆就不管了。”有的地方两派互斗,下乡不久的知青成了局外人,工分口粮一切无人理睬,也只有回城一途。
还有的知青,参与了当地的群众组织,因为他们毕竟是城里人,见过世面,与仍然在城里的同学、家长,保持着各种联系,比当地人能听到更多的“小道消息”笔者当年曾在河北省宝坻县一个从天津高中毕业后到那里插队的知青炕头,见到厚厚一叠北京各大学的油印小报,据他说,都是他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寄给他的,这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某派能否取胜的关键。,这些知青因此而在群众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有的互相进行串连,有的则以这种身份进驻到城市,在城市设立了“联络站”。
各地农场或农村人民公社对知青的态度,同样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对知青已经无暇顾及;有的摸不准中央到底持什么态度,唯恐知青将火烧到自己身上,而有意放纵甚至动员知青回城。城市的当权派,因未得到中央的明确表态,也不知对这一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才好,只能以支持群众造反的总方针笼统待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总之,当时敢于劝止或“阻挠”群众进行“革命串连”的领导,是极其罕见的。 。。
返城风潮(3)
这种支持,当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许多地方的知青,合法地取得了与在校师生一样的串连待遇。例如当中央于1966年11月16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通知》时,广西自治区的“党委群众接待站”就曾拟定了一个计划,规定凡学校师生、下乡知青,或机关干部参加长征串连的,每人每月都由自治区补助7元人民币和45斤粮票《广西###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再如插队知青相当集中的上海郊区金山县,曾从地方财政中一次签发“串连费”50多万元;很多地区发给知青路费,予以各种方便,如据黑龙江省巴彦县的知青说,“###”一开始,当地的“一小撮走资派”就煽动知青回城串联,还发给每人300块钱,让他们回城另找工作。这些钱,正如中央所要求,都是从国家或地方财政中开支的。
最甚的是新疆。新疆为参加“大串连”的师生和群众所发放的补助都堪称优厚,并不是仅仅对知青才是如此,乌鲁木齐市有中学生描述当时情形说:
从去年(即1966年)12月开始,新疆地区出发的长征队很多,尤其今年以来更多。不少地区给长征队发了许多东西,如上好的皮大衣、皮帽、鞋、棉衣、棉裤、水壶、裹腿、手电筒及各种补助费等。由于长征人数很多,沿途每隔二、三十公里就设有接待站,每个接待站各有几十床以至上百床新棉被等,并派专人接待……有的地方接待不了那么多人,就想办法用汽车送往别处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六六?八八”战斗队造反长征队:《打回老家来,就地闹革命》,《新疆日报》,1967年1月17日。。
很难想像远离家乡的上海知青能抵御这种声势和###。
满怀献身热情的上海知青到新疆之后,才发现边疆并非尽如《军垦战歌》描述的那般如诗如画,他们抱怨说,兵团的劳动非常繁重,到摘棉花的时节,每人每天要完成定额100多公斤;有的师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根本不适宜开垦,结果苦苦干了几年,却发不出工资;兵团中有的干部对知青十分粗暴,甚至私设公堂,有40多种刑法;女知青的人身安全、婚姻自由得不到保证,有的人竟公然提出“兵团姑娘对内不对外”的口号,很多知青感到后悔,想方设法要回上海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最初是极力阻止知青串连出走的,据驻在南疆喀什的农三师知青回忆说,当时兵团领导在沿路设卡,查验通行证,没有通行证,谁也走不了,但当“大串连”风潮终于掀起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抵挡了。1966年底,他们发出了一个《处理支边青年回原籍搞###的四点指示》,据当时报刊的批判,这个指示“煽动支边青年离开新疆回原籍,还勒令回原籍搞###的青年统统把户口带回家去”《新疆日报》,1967年2月1日。。
从《新疆日报》后来刊登的一些批判稿所透露的情况,可以窥见这场返城风的凶猛程度:
阿克苏丰收农场七连“革命造反团”的部分支边青年说:“地委利用了部分群众的革命热情,开证明,给路费,给皮大衣和毡筒,放走了大批支边青年。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见到如此容易外出,以为中央有了指示,于是大批大批的人都走了,仅元月1日至5日的5天内,地委就给我们农场要外出的人发放经费2万多元。大批人一走,有的连只剩了二三十人,各连负责人一个个跑到阿克苏,饱食终日,消闲无事,地委的问题也无人去追了……”《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打退经济主义的猖狂进攻——致全疆支边青年的一封信》,《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
返城风潮(4)
新疆八一农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说:“畜牧厅农场有380名支边青年,这次外出‘串连’和‘告状’的就有253人(其中有31人是不告而去的)。农场的当权派给他们发路费和生活费(补助费)共计27000元。农田九队原有80人,现仅剩十几人,生产完全停顿。这是经过畜牧厅某副厅长、自治区党委农工部某副部长层层请示,最后由自治区副主席田仲批准走的。再如水利厅牧区水利队400人仅剩80人了。有的单位连锅炉工、炊事员都走了……一些人领上串连装备后把钱花了,甚至戴上新买的手表,穿上新衣新鞋,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