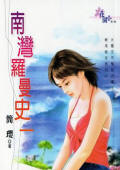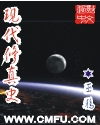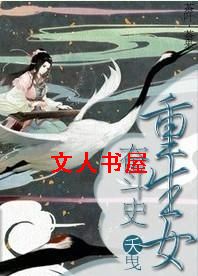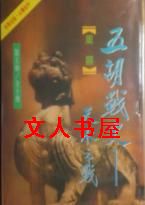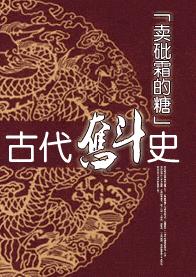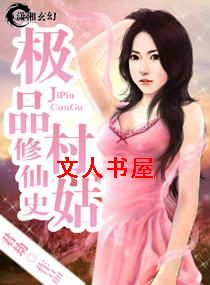中国知青史-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法乱纪分子,不论资历高低,职位大小,都必须严肃处理,不得姑息迁就,情节严重的应依法严惩。如系地、富、反、坏分子,更须加重治罪。《农垦部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纪律规定》,1964年10月21日。
这是迄今可以见到的“###”前对于这类问题最具体、最严厉的一份纪律规定,它对于那些为所欲为的农场干部,无疑是有震慑威力的,但它毕竟不是法规,而且下面一旦具体执行,就有松有紧了。
从1965年农垦部党组向中央所作的关于湖南省湘阴杨林寨、江永县回龙圩、铜山岭、桃川等4个农场歧视、虐待和侮辱下乡青年的严重问题的检查报告来看,这一规定并未能有效制止该部所属农场中此类犯罪事件的发生。当时中央对此问题所作的批示说:
农垦部这个检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主要是严重违法乱纪、干部压迫、剥削青年,对下乡青年生活漠不关心。这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如果不把这些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整好,那么,这些农场的领导,就永远会同贫下中农、同下乡劳动的青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就不会办好社会主义农场。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6)
批示还要求各地把所属农场的工作都检查一次,对这类违法乱纪的行为,应在查实后严肃处理《###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湖南有些农场干部###下乡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1965年5月20日。。
从这份批示看,即使是中央,对下面干部的这些作为,也没有明确认为是在犯罪,而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既然严重违法乱纪、压迫剥削青年的行为,都只不过是“官僚主义”,至多也不过是“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话,那么干部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农垦部对于这类问题,还是重视的。它所属的国营农场,毕竟属于“王法”可以管得到的地方,而在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地方农场,问题则更为严重。即使在中央有关文件发布之后,仍然是“尚未引起领导重视”。按照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于1965年4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既不上报,也不检查处理。还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严重污辱和###下乡青年的案件,不告不理,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议认为,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可见,在其他有些地方,问题可能比农垦部所属各国营农场更严重。
这类问题在农村生产队也同样存在,只是表现方式略有不同而已。除了像农场一样对知青政治上歧视之外,主要表现在与社员同工不同酬、劳动强度大和女青年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几个方面。亦即如当时中央文件所指出的,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劳动“底分”过低,加之生产队派工不合理,同工不同酬,生活不能自给;有些年少体弱的青年,因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而影响健康,特别是有些水田地区,百分之###十的女青年患妇女病,甚至发生死亡事故。这是在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农民的物质生活在当时已经十分贫困,但有些地区的知青,甚至达不到一般农民的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不愿知青分沾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城里人”的一种敌视心理。有的地方对知青在劳动上要求过急过高,甚至专派重活给他们干,理由便是“让他们尝尝当农民的味道”。据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如陕西扶风县黄浦公社89%的回乡青年口粮都比一般社员低,而且质量差。又如不少地方给知青的自留地分得很少甚至不分,有的地方按社员一分五、知青一分的标准分配自留地,甚至如安徽肥东县电站大队从1963年冬到1964年春回乡的4名知青,到5月还没分到自留地。还有很多地方的知青,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能住到生产队的办公室或仓库甚至马棚里。
插队女知青与农场女知青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央文件谈到:
现在,有不少下乡青年,尤其是女青年,早婚的很多,对他们的进步、劳动影响很大。应该加强晚婚节育的教育。有的地方发生过逼婚、骗婚、污辱妇女的现象,应当及时处理,并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类问题。《###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1964年4月24日。
如果说国营农场尚有国家的纪律管束的话,对于农民,则连这点约束都难以奏效,事实上直到“###”以后,对于下乡插队知青的处境,始终无人能拿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7)
总之,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为了能够将这场运动顺利地、长期地进行下去,国家就十分重视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但是始终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种种政治、经济的大原则的制约之外,关键在于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知青无法将保护自己的“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只能企盼于“上面”的眷顾,即靠得到中央的注意和中央发布文件。而中央即使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再大,做法再严厉,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阵风。大风刮过,依然故我,这已是多年来干部群众都习以为常的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结果便是知青的状况,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期间这类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直至中央不得不采取将几名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以平民愤的方式,却仍然无法杜绝,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四清”运动的开展,使知青在农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
1963年5月###中央印发《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后的1964年9月,中央又发布有关这次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规定这次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在农村引起巨大震荡的“四清”运动,下乡知识青年也受到这场运动的深刻影响。许多工作组将农村中组织阶级队伍等一系列做法运用到知青身上,结果,第一是使一部分青年被作为运动的依靠对象,参与了对当地干部的斗争和冲击,恶化了与干部与社员的关系,甚至到了难以在当地立足的地步;第二是使相当多出身不好或有一些不良习惯的知青,被当作阶级敌人和被整顿清理的对象,遭到打击;第三,它也使知青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恶化了。
我们这里引几个当年四川知青的回忆为例:
1964年4月从成都下到四川省会理县鹿厂公社的知青回忆说,当年收完大春后,县里来了知青整顿工作组,把鹿厂公社209个知青统统集中在公社进行整顿。七整八整,有个14岁的小知青被整得魂飞魄散,哭着交代了曾偷砍生产队的包谷秆吃,还偷盖公章私自开条子到公社割肉吃的“罪行”,然后在身上一无钱、二无粮的情况下,横越大渡河,竖攀万丛山,历时一个月,硬是一步一拖回了成都黄新生:《杨瓜娃儿》,《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工作组还将知青按照出身不同划成三六九等,1964年从四川合州下乡的知青回忆说:
知青农场办起没到一年,便驻进了四清工作组。于是,农场一百几十号知青顿时分了等级,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立马有了区分,对红、黑两类出身的知青召开了内容及形式都不同的会。
工作组长是位湖北佬,复员军官,说起话来声震屋瓦。他的口头禅是“枪打出头鸟”,每说此话时,二目放光如手电筒般四射,使人心惊胆寒。依了这位工作组长的分等划类,我们农场里便有了一个应予诛灭的黑帮,这个黑帮由27名黑五类子女构成,为首者便是其父解放前曾任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的何姓知青,被定为农场最大之黑堡垒,由工作组长组织知青围而攻之。戴克学:《老知青###读书梦》,《龙门阵》,1993年第4期。
更有甚者,1963年10月,曾有300多名成都知识青年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叙永县后山茶场落户,一年以后,省、地、县三级的“四清”工作组进驻茶场,不知出于什么背景和动机,便将这批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的知青“娃娃”当成了妄图变天的阶级敌人:
县委工作组长,一位姓王的局长有一次对二队的同学们训话,竟说:“不怕你们这些成都娃娃,你们休想变天!我们有监狱、警察、军队,还有飞机、坦克、大炮。”接着,背靠背的揭发、检举、批判会陆续开始了。
很长很长时间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动用那么多人,无缘无故地来对付这几百名种茶的少年,扼杀他们青春的梦想,把他们之中的数十人,直接投入罪犯和贱民的地位,饱受人格的屈辱,丧失青春、幸福、健康,乃至生命。而谁都知道,确定不移地知道,这些人是无罪的!余下的两百多人,无疑也饱受惊吓,紧接着又带着受伤的心灵,接受了随之而来的“###”的洗礼周永严:《下乡周年祭》,《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 想看书来
回乡知青的处境(1)
与城市知识青年一样受过学校教育,然后一样上山下乡的农村青年,也就是“回乡知青”,人数始终多于城市知青。虽然他们并未被国家划入安置工作的范围之内,对于动员他们回乡,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长期工作以后,也几乎不再成为问题。但他们回乡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惑,从性质上说,与城市青年是一样的。这里之所以将他们专门列为一节,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也存在一些特殊问题。
虽然国家自1954年起就大力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但回乡知青数目的迅速增长,是在1960年以后。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青年回乡的走向可以用上下波动的###表示的话,60年代以后则一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了。这当然是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紧密相关的。
1958年《户口管理条例》的实施,城乡间裂痕的扩大与加深,都大大减少了农村到城市谋求职业的可能性。甚至原先许多农村女青年通过嫁给城里人而改变自己身份的出路,此时也被基本堵死。因为即使与城里人结婚,也极难改变原来的农村户口,而且如果母亲是农村户口,孩子即使是在城里出生,户口也要随母亲一方,并且会随之遇到诸如没有粮食副食供应、无法在城市入学等一系列困难。
于是,农村青年想要成为城里人亦即获得城市户口的途径,便只剩下三个,一是参军,二是当干部,此外就是读书、升学。只要读到中专、大学毕业,自然就可以由国家将工作包下来,当然也就获得了城市户口。而参军,大多数人复员后仍需回乡,提干只是极少数政治条件好的人才能得到的机会,而且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可见,考中专、读大学,是农村青年实现自己当城里人、挣工资并进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选择,也是当时农村青年的家长最大的愿望。为此,许多父母不惜节衣缩食,卖猪卖粮,送子女到学校去,而当这些子女苦读数年,甚至十数年之后,又回到家乡种地时,其父母的失望、愤懑和对这个事实的不能接受,都是不难想像的。
可是,对农村子弟来说,走读书这条路,到60年代以后也越来越艰难了。在第六章谈到过,国家于1960年作出规定,为了保证农村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不断补充农村劳动力,此后必须在每年毕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中给农村留下一定的比例,不要全部升学。按这个比例规定,能够升学的农村中小学生只有1%,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学生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从农村考入大专和中专的学生,在学校停办后也被一律要求回乡,而这时数量特别多的还有几乎全部停办的农业中学的学生。这都造成愈来愈多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不得不回乡生产的局面。
据团中央1962年统计,全国农村已有高小以上知识青年近3000万人,大体上在1亿农村青年中,4个人中有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生。1964年,全国知识青年总数达4000余万,其中城镇下乡知青仅几十万,在知青总人数中仅仅是一个零头,其余的,都是回乡知青。再举几个具体数字:据北京市的统计,到1962年底,参加郊区农业生产的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回乡知青达11万余,约占郊区农村青年总人数的1/3;上海市川沙县统计,自1957年到1964年期间,陆续落户、回乡的知青达52000余人,占全县农村青年总人数的2/3以上,占全县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4以上,有的公社70%以上的农活是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