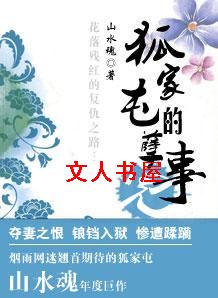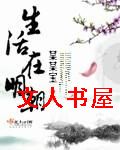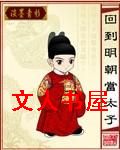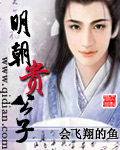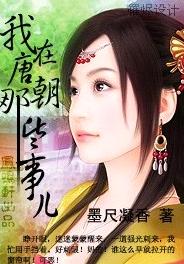明朝那些事儿(全集)下-第1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1761' 自打追缴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印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
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消息:张献
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
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
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
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1762'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
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
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律,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
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
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
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1763'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
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弁度,都可
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
辜负他的信任。 选择,没有选择 杨嗣昌死了,崇祯很悲痛,连他爷爷辈的亲戚(襄王)死了,他都没这么悲痛,非但没
追究责任,还追认了一品头衔,抚恤金养老金,一个都没少。知己死了,没法以死相报,以钱相报总是应该的。 其实和崇祯比起来,杨嗣昌是幸运的,死人虽说告别社会,但毕竟就此解脱,彻底拉倒。 而崇祯是不能拉倒的,因为他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崇祯十三年(1340),崇祯正忙着收拾张献忠的时候,皇太极出兵了。 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出兵,但这一次很不寻常。 因为他的目标,是锦州。 '1764'
自打几次到关宁防线挖砖头未果,皇太极就再也没动过锦州的心思,估计是十几年前被
袁崇焕打得太狠,打出了恐 x症,到锦州城下就打哆嗦。 所以每次他进攻的时候,都要不远万里,跑路、爬山、爬长城,实在太过辛苦,久而久之,搏命精神终于爆发,决定去打锦州。 但实践证明,孙承宗确实举世无双,他设计的这条防线,历经近二十年,他本人都死了,
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折腾皇太极。 皇太极同志派兵打了几次,毫无结果,昀后终于怒了,决定全军上阵。 同年四月,他发动所部兵力,包括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甚至连尚可喜、孔有德的汉
奸部队,都调了出来,同时,还专门造了上百门大炮,对锦州发动了总攻。 守锦州的,是祖大寿 事情的发展告诉皇太极,当年他放走祖大寿,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这位仁兄明显没有
念他的旧情,还很能干,被围了近三个月,觉得势头危险,才向朝廷求援。 而且据说祖大寿的求援书,相当地强悍,非但没喊救命,还说敌军围城,若援军前来,
要小心敌人陷阱,不要轻敌冒进,我还撑得住,七八月没问题 但崇祯实在够意思,别说七八月,连七八天都没想让他等,他当即开会,商量对策。 开会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要不要去,二、派谁去。 第一个问题很快解决,一定要去。 就军事实力而言,清军的战斗力,要强于明军,辽东能撑二十多年,全靠关宁防线,如
果丢了,很没戏了。 第二个问题,也没什么疑问,卢象升死了,杨嗣昌快死了。 只有洪承畴。 问题解决了,办事。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洪承畴出兵了。 得知他出兵后,皇太极就懵了。 打了这么多年,按说皇太极同志是不会懵的,但这次实在例外,因为他虽然料定对方会
来,却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多。 洪承畴的部队,总计人数,大致在十三万左右。属下将领,包括吴三桂、白广恩等,参
与作战部队除本部洪兵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昀能打的,他基本都调来了。
本来是想玩玩,对方却来玩命,实在太敞亮了。 '1765' 考虑到对方的战斗能力和兵力,皇太极随即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
敌军进攻。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很晕。 因为洪承畴来后,看上去没有打仗的打算,安营、扎寨,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再吃饭,
再睡觉,再不就是朝城里(锦州)喊喊话,兄弟挺住等等。 晕过之后,他才想明白,这是战术。 洪承畴的打算很简单,他判定,如果真儀真枪拼命,要打败清军,是很困难的,所以昀
好的方法,就是守在这里,慢慢地耗,把对方耗走了,完事大吉。 这是个老谋深算的计划,也是昀好的计划。对这一招,皇太极也没办法,要走吧,人都
拉来了,路费都没着落,就这么回去,太丢人。 但要留在这里,对方又不跟你开仗,只能耗着。 耗着就耗着吧,总好过回家困觉。 局势就此陷入僵持,清军在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隔几十里地,就不
打。 当然,清军也没完全闲着,硬攻不行,就开始挖地道,据说里三层、外三层,赛过搞网络的,密密麻麻。 但事实告诉我们,祖大寿,那真是非一般的顽强,而且他还打了埋伏,之前跟朝廷说,
他可以守八个月,实际满打满算,他守了两年。 就这样,从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到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双方对峙一年。 六月底,开战了。 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出兵,向松山攻击挺进。 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的意料,清军总指挥多尔衮(皇太极回家)没有提防,十万人突
然扑过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败。 消息传来,皇太极晕了,一年都没动静,忽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 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
松山。 但是,有个问题。 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 一般说来,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拿张手纸塞着,也还凑合。 但皇太极的这个鼻血,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没个停,连续流了好几天,都没办
法。 但军情紧急,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病工作,骑着马,
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 '1766'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了个碗,就放在鼻子下面,一边骑马一
边接着,连续两天两夜赶到松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 反正我是到今天都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 会战地点,松山,双方亮出底牌。 清军,总兵力(包括孔有德等杂牌)共计十二万,洪承畴,总兵力共计十三万,双方大
致相等。 清军主将,包括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精锐将领,除个把人外,都很能打。 洪承畴方面,八部总兵主将,除吴三桂外,基本都不能打。 至于战斗力,就不多说了,清军的战斗力,大致和关宁铁骑差不多,按照这个比率,自
己去想。 换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