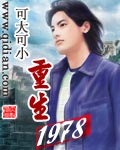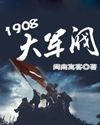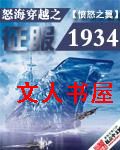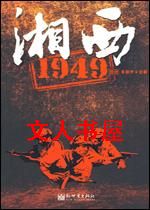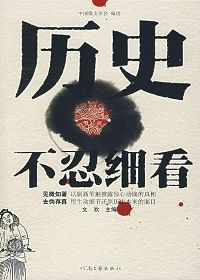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们分道扬镳吧。”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老一少的话都没有说错。
那个冬天的中国饥寒茫茫,乡下大约只剩下三样东西:“共产主义天堂”的梦想、揭不开锅的食堂和饿死路边的农民。毛泽东正在广州加紧搞他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身边聚集着当日一群最有学问的人,包括陈伯达,他是这一文件的捉刀者之一。可是,还有另外两个不知名的乡村小人物,也坐在自己家中埋头写作。
二十七岁的冯志来在1962年4月21日完成了他的文章,题为《半社会主义论》。文章劈头就问:
“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是单干”,他嘲笑那些把“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人”,“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这样的讽刺已经足够使人恼怒,然而他还轻蔑地说,“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照过去方针办(24)
在写了这些之后,他凑了一百六十块钱,就在那个春天里搭上一列火车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送了两份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是党报和党刊,其中任何一家都可以直接上达毛泽东的视听。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居然没有人来理睬他。
被轻蔑激怒了的小人物回到家里再接再厉。过了两个月,6月30日,他又写出一篇,叫做《怎么办?》,说是为了补充他的那篇《半社会主义论》。他的新作是一篇###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笔锋犀利地直指农村里的悲惨局面,仰天长问:“错在哪里?”人们都说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的错误……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都得到鼓励,在高速度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夺农民。大跃进变成大倒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他那时还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却懂得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再一次把这些文章投递北京的时候,他自称自己乃是冯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愿,北京的回信来了,可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当地党的机关,要他们追查信作者的后台是不是冯雪峰。
然而《人民日报》那时接到的信可不仅仅是冯志来一个人写的。另外一个人,陈新宇,写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里务商,因为向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蓝图,高喊着“我爱农村”,就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队伍。结果他看到农民对于公社根本没有兴趣,却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就一气写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报》。他告诉报纸编辑,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现在坚决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回编辑居然大动侧隐之心,将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个叫做《读者来信》的不公开的刊物上,并且加了一个标题:《重谈包产到户》。陈新宇说他“确信包产到户是终将出现的必然的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像冯志来一样,他闭门拒友,坚持独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时候;乡下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东西的人多得出奇,可是能够把它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并且公诸于众的,只有这三个人。显而易见,包产到户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行动,而且让这三个人找到了不少理论根据。这使得农民对人民公社发起的挑战更加有力。几十年后,人们终于发现这几个小人物的见识远远高于那些大人物。这三个人都出自浙江,又都不谋而合地采取了犯颜直谏的行动。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口气之严厉,令人心惊肉跳。不过,真正的狂风暴雨还没有到来。7月中旬,陈新宇还接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共计二十五元五角。这迹象多少让人觉得轻松。他将稿费买来一大堆桃子分给同事,一时间他的周围竟有了笑声。但就在这时,风云突变。
冲突的导火索是由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点燃的。此人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本来深悉毛泽东的心理,亦持有同样的反对包产到户的倾向。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到他的故乡湖南去作一番调查,这是1962年早春时节,乡下适为包产到户的高潮,毛泽东也许是希望他能提出一些有利于人民公社的证据。不料田家英这一去就完全站到了包产到户的一边,农民对于包产到户的热烈情绪令他感慨不已。但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报告,而是依次向政治局中最主要的成员游说他的想法。
毛泽东不打算过早地干预这件事情,他只含糊地表示,包产到户只不过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共产党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然后就稳坐如山,静观事变。他的同事们却按捺不住了。陈云称赞田家英的看法,并且决定向毛泽东当面进言。他向毛泽东建议,“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克服农村困难”。邓子恢在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他把这封信以及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直接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在京城里到处做报告,说“农村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办到的。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还说“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但是他用不了多久就什么也说不了了,因为他被解除了农村工作部部长之职,罪名是专“刮单干风”的“资产阶级农业专家”。
照过去方针办(25)
那时的中央书记处对经济的事情是不能沉默的。邓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看来邓小平打算用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对待眼前这场争论。他解释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说了一些外圆内方的话。比如说“赞成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的要求总有道理”,“新生事物,可以实验”,等等。他明里不说他的倾向,但这些话让人一望而知他是包产到户的支持者,可是却又打他不中。(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23页。)
刘少奇的情况有一点复杂。他在这两年里担负着权力机构中的主要角色。在他执政期间,他先是纵容包产到户的实际进展,接着又怂恿田家英向毛泽东去进言,他甚至还曾明确表示“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这些来自最高领导核心的方针导向,无疑正在构成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威胁。但是,刘少奇的这一立场,实际上只保留到这一年的7月18日。依据官方文书记载,这一天他对一批即将到乡下的干部发表演说,严厉地批评“包产到户”,还说这证明从中央到基层都有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又过了三个星期,他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对农村的困难“估计过分了”。这些情节后来无论在反对他还是同情他的人中均被忽视,其实刘少奇的进退转圜在权力中枢至为典型。以当日国家的危机情形而论,党的高级官员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务实立场来处理国家大政,否则就不仅是农民进一步的大批死亡,还会危及整个党的生存。当然这只能维持在一定限度。事态的进展逾越限度,就得以变通来代替原则。这中间的原则与变通,智慧和愚蠢,都有着恰如其分的理由。
应当说,直到此前的两年,毛泽东一直都很温和。据他身边的人回忆,他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度不置可否,甚至表示“可以在小范围里实验”。可是,人民公社毕竟是他的心血结晶,上下左右联合起来加以攻击,就令他再也不能容忍。
整个8月,政治局会议上一片紧张气氛。毛泽东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质问他的同事,不断地打断人家的话。语气中充满应战和挑战的尖刻与激昂,真是怒火中烧。他指出单干之风越到上层就刮得越大:“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但是假如仅仅是乡下的混乱,还不至于让他这样恼火。问题是“这股风从何而来?”他自问自答:来自党内。他认为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包括贫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地主,还有知识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还有人出身封建官僚。“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热闹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他的同事听到这些,就有点不知所措了。但是毛泽东还没有完。他厉声道:“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一番话更说得众人闷声不语。又过了三天,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只不过怒火更甚:“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当日在场的薄一波回忆说,从这以后,政治局里就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所有人都变成“单干风”的坚决反对者。那个夏天可真是政治成果的丰收季节,很多东西是共产党历史上之首创。比如资本主义倾向说,资产阶级复辟说,反对翻案说,前途光明说,阶级斗争再搞一万年,以及党内会出修正主义,儿子不出,孙子出……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再一次迫使他的同事纷纷检讨,接着一起举手同意他的方针。
60年代初期风行乡村一亿农民中间的包产到户,终于再度沦为非法。一场批判运动由此发动起来,据说受到牵连者多至四百万人。“浙江三杰”自然首当其冲。冯志来由武装警察押解回乡,在监督之下劳动改造,终日沉默寡言,却身怀一百粒安眠药片,昼夜不离,随时准备赴死。直到十八年后,也即1979年,冯看罢话剧《于无声处》,大哭一场,满腔悲愤,喷薄而出。这是他平生第二次大哭,前一次是在1958年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籍被开除的时候。杨木水于次年被逮捕,刑期八年,与死囚同监。杨不甘受辱,于是大骂林彪,以求死刑。次日果然成为死囚,负十八公斤铁镣等待处决。恰在这时,林彪垮台,杨木水得免一死,但仍然加刑四年。陈新宇是被毛泽东亲自指名的“单干理论家”,故处境更加悲惨:七次抄家,一百二十次批斗,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自认“迷天大雾终须拨尽,春照丽日还教重来”。他不停地写信上告鸣冤,连续二十年,总计二百余封。待到真的“迷雾拨尽”、“春照丽日”之时,他已是一个干姜一般的小老头,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只余满脸皱纹,宛若斧劈刀凿。
毫无疑问,刻在这些“单干理论家”脸上的斑斑痕迹,也会刻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中间有着一个“大同”制度的美好初衷和惨痛结局,以及“包产到户”这一抗上行为的险恶遭遇和巨大牺牲。无情的现实,究竟还能让这一悲壮的历史持续多久呢? 。 想看书来
大梦谁先觉(1)
五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人辞世长卧,令我们庞大而又古老的国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又如坠五里雾中,那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都弥漫起这一种感觉。但是,历史的交汇点此刻被装在一个信封里,竟是大大超过世人所料。
l月1日凌晨,整个中国还在睡梦之中,一个搬运工人从床上爬起来,揉揉眼睛来到北京火车站上,把这一纸书信和着一大堆邮包,塞进一列火车的邮政车厢,然后照往常一样,甩甩手就走了。这信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此刻正随车向南京而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无奇。《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在这封信中告诉他的作者,文章已经编定,寄还征求意见。信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