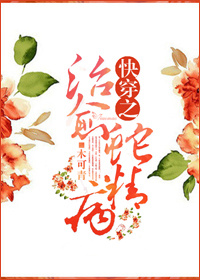文景之治-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吏,在主子发家致富的过程中都立过汗马功劳,所以主子夸富,他们也觉得与有力焉、与有荣焉的缘故罢!
刘太公则一张老脸羞得通红,看来自己的眼光确实不行,老二确实不中用,给他个代王做,他都没能力。当然也有些自豪,不管怎么样,眼前的皇帝究竟还是自己的儿子嘛,是自己在床上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嘛,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看走了眼也不会死嘛,自己眼光虽然不行,精子质量终归还可以嘛。要不,能生出皇帝来吗?
当然,刘太公的想法,是按照科学推理来说的。但他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在《史记》和《汉书》里,他的这一制造权被史官粗暴地剥夺了。史官们信誓旦旦地说,刘邦这个儿子,是刘太公的老婆刘媪和蛟龙交配出来的,和刘太公丝毫没有关系,他顶多算个假父。我不知道现在要是能起刘太公于地下,他会不会嚷着去做DNA化验,看看刘邦的生理学父亲到底是谁,是那条谁也没见过的蛟龙吗?还是生活在侏罗纪的恐龙?
可能因为老爸的认错态度还可以,刘邦对二哥的那种耿耿于怀逐渐消除了。十一年的秋天,英布举兵反叛,击灭了荆王刘贾,关中震动,刘邦不得已亲自出征。
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二十岁,跟从出征。他长得非常强壮,擅长骑射,在这场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到击灭英布为止。
七国起兵晁错丧(2)
英布死后,刘邦有些忧虑,原来的荆王已经被杀,得重新立个国王才行。那时的地域歧视很严重,就像现在河南人被妖魔化了一样。中原人普遍认为吴楚人都是愣头青,喜欢打架斗狠造反,不在这里立一个擅长打仗的王恐怕镇不住。刘邦想,自己的儿子都还小,没办法胜任。刘濞这次的表现不错,是个上好人选,于是封刘濞为吴王,管辖东阳郡、吴郡、故鄣三郡五十三城,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
刘邦命令把吴王印绶授予刘濞之后,又亲自召见了刘濞一回,这回他左看右看,发现刘濞的相貌有些不对,对刘濞说:“你长着一副造反的相啊!”心里非常后悔。但是印绶已经给了,再收回也不大好,何况是自己的亲侄子,于是拍拍他的背,说:“大汉五十年后,东南方有造反的人出现,难道就是你吗?不过我们都是同姓刘家,你可一定不要造反哦!”
刘濞赶忙顿首道:“岂敢岂敢!”
当然,上面的肯定是传说,刘邦怎么可能预见五十年后东南有兵灾,也不可能看相就知道刘濞会谋反。史家把这种事也堂而皇之地记载在史书中,大概就是想说明刘邦是天子,非凡人可比。
吴国是块好地方,地方大,风景好。海边可以煮盐,所辖的故鄣郡(今安徽、江苏南部以及浙江西北一带)内有铜山,可以铸钱,靠着盐、铜的资源,吴国非常富裕,根本不需要向老百姓收取赋税。而且招纳了外郡很多亡命罪犯,收归己用。因为没有赋税,百姓对刘濞也非常拥戴。
刘恒即位后,刘濞曾经让自己的王太子刘贤代替自己去长安朝会。刘启和刘贤年龄估计差不了多少,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刘贤的师傅都是吴楚人,依照地域歧视观念,教出来的学生也肯定是愣头青。刘贤和皇太子玩博棋,输了就饮酒,本来应该谦恭一点,可是他偏不,有一次出现了争执,坚决不肯让步,刘启可不像他老爸那么温文尔雅,再说自己是大汉皇太子,怎么肯受小小的吴王太子的气,当即勃然大怒,提起博棋的棋盘就猛地向刘贤掷去,刘贤猝不及防,被棋盘砸中,当场毙命。
皇太子杀了吴王太子,这能有什么办法?难道还能将储君治罪?刘恒于是命令将刘贤厚敛,再运回吴国归葬。
吴王刘濞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站着去长安,躺着回吴国,伤心欲绝,却也无可奈何,总不能要皇太子偿命。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够贵,没当上皇帝,让爱子白白死了。他是个打仗出身的人,性情刚猛,心里的怨恨容易浮在脸上,不懂得收藏。他看见儿子的丧车回来,想起了当年刘邦说的那句话,怒道:“既然天下同宗,都姓刘氏,那么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好了,何必把尸体运回来?”又命令把丧车重新运回长安。这时的吴王,大概在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个心愿:有机会一定要杀回长安去,亲自到爱子坟前祭奠。
从此之后,刘濞心都碎了,再也不愿去长安朝会,每次新年都称说病重,经不起路途颠簸。可是哪有几十年如一日都称病的?长安的官吏都知道他心里因为爱子的死而怨恨装病,于是吴国使者一旦来了长安,都全部拘押责问。刘濞也很惊恐,当即加快了谋反的步伐。
后来刘濞又派使者代替自己去长安作例行的秋请之礼,刘恒亲自责问使者:“为什么刘濞不肯亲自来?”吴使者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大王确实没有生病,因为汉朝几次拘押了吴国的使者拷问,我们大王心里愈发害怕,所以称病。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如今我们大王装病的事实陛下已经知道,可是能怎么办呢?陛下要是将我们大王责问急了,他就更加想不开,怕被陛下诛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造反都不行了。臣以为陛下不如忘掉以前的不快,和我们大王重归于好。”
刘恒想了想,觉得这个使者很聪明,说得很有道理。虽然自己在长安地位已经逐渐稳固,但逼得吴国造反到底合不合算?万一镇压不下去,自己的皇帝宝座能否坐得稳,实在是个未知数。不如先笼络吴王,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代去考虑。于是把以前系押的几批吴国使者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国,并且赐给刘濞几杖,说尊重老年人,准许他可以不用来长安朝请了。
七国起兵晁错丧(3)
刘濞没想到刘恒这么好,既然汉朝不逼迫,自己又何必造反,究竟汉强吴弱,自己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逐渐打消了造反的念头。他继续在国内推行不收赋税的政策,老百姓按照法律要被征发戍边,吴国政府也出钱帮老百姓雇人代替。他还经常亲自访问闾里百姓,赐给他们食物和金钱,别的郡国逃亡来的罪犯,吴国也特意隐藏起来,不交给别国要求引渡的官吏,这样总共过了四十多年,吴国经济蒸蒸日上,刘濞更加得到了吴国人民的爱戴。造反的潜力非常强大,就等待催化剂了。景帝三年,这个催化剂终于不速而至。
壹
刘启即位的第三年,以吴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南方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历史上称它为“七国之乱”。
在谈七国之乱前,我们还得说说前两年刘启做了些什么事。
在景帝元年的冬十月,刘启下了一道诏令,列举了老爸刘恒的许多功德,决定要给刘恒制定庙乐,命令群臣讨论一下,具体怎么实施。
群臣立刻集体上书,说不但要给文帝立庙乐,而且还应该制定庙号。他们认为,功劳没有大过刘邦的,德行没有盛过刘恒的,因此,高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宗之庙。所以他们二者的庙,不但应该立在长安,在天下郡国都应该有,而且要按时派使者祠祀。所谓“太祖”、“太宗”,就是庙号。
说起庙号,必须谈谈它跟谥号的区别。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对他盖棺论定一下的,这风气据说出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死了的姬昌和姬发摆摆功劳。结果是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了。这名目叫做“谥”。“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对一人的盖棺论定,别想翻案。
谥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章太炎在他的《訄书·平等难》里说,众生平等是虚假的,人的身份总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就说民主典范的美国吧,要把乔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来,事实也办不到,并非每个人能像布什老爸那么阔,花足钱让他念名牌大学乃至推上总统位置的。不过章太炎说,绝对平等虽然不可能,绝对的批评却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谥”这个例子,说老百姓对他们的王可以置褒贬,有罪的王,史书上不得不留下那么丑恶的一笔。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犯了大过错老百姓不满意,则连躺进金字塔的资格也没有,煞是可怜。因此这惩罚很能让生前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作歹。可见谥号的作用。当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着谥号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大,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费心力去褒贬你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符合经济规律。《大戴礼记》里说:“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惧;匹夫之怒,适以亡身。”这是很经典的概括,对我们现在还适合。比如一个县长对县公安局长发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县公安局长只有胆战心惊地照办,哪怕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可是一个平民如果因为自己老婆被县长玩弄了,就想学吴三桂冲冠一怒去杀县长,很可能是找死。“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浪漫的爱情,在吴三桂则可,在我辈则不可,因为力量悬殊。为了心理平衡,我们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谥号这玩意当救命稻草捏在手里,希望君王贵族们发号施令、生人杀人、欺男霸女时能有稍微收敛。
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账,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像周朝的 “厉王” 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七国起兵晁错丧(4)
在先秦,这谥号制度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春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群臣劝说了五次,都不管用,只好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令尹(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恭”和“共”音近同源)。”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暴君秦始皇是看到了这一层的,他讨厌谥号,所以一并天下,自我膨胀得要命。改了王称“皇帝”还不够,还下诏要废除谥号制度。理由是“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他多有野心,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结果只落得二世而亡。这“二世”虽不算谥号,可比所有的恶谥还臭。后世说起灭亡的例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所以,在谥号之外,就必须搞出一个更高的荣誉,这就是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