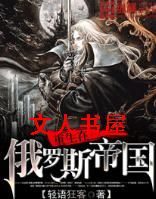从苏联到俄罗斯-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尊敬他。‘他怎么看待你画的画?’‘他很喜欢。’另一位画家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画家,完全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不相同。我们在出版社做了许多工作。别柳京帮助我们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表现在画布上,我们非常感谢他。’‘好吧,现在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说。我用最通俗的话给他讲解绘画艺术,赫鲁晓夫默默地听着,一场风暴可能过去了。但这时,苏斯洛夫低下头,对着赫鲁晓夫的耳朵说了些什么,赫鲁晓夫看了看我平静的脸,突然爆炸了:‘你说什么?这怎么会是克里姆林宫呢?这是对它的嘲笑。墙上的雉堞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太笼统和无法理解了。别柳京,你听着,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对你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苏联人民所需要的。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苏斯洛夫转过身来,指着米罗诺夫画的沃利斯克风景画问道:‘这表现的是什么?’‘沃利斯克市’,我回答道,‘生产水泥的城市,那里到处都覆盖着一层灰色粉末,可人们仍然出色地工作,仿佛没注意到粉末。’‘你怎么说有粉末呢!你到过沃利斯克没有?’苏斯洛夫喊起来。‘这不是虚构,而是写实。’我回答道,‘您可以调查嘛。’‘那里干活的人都穿白大褂!干净极了。’苏斯洛夫继续喊道。白大褂……我记得那座灰色城市,树都蔫了。几公里以外都能看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灰尘。‘这是什么工厂?画的是《红色无产阶级》工厂,是吧?怎么那么多烟筒?这个工厂只有四根烟筒。’苏斯洛夫仍不甘休。他故意装作愤怒,表明他同赫鲁晓夫的看法完全一致,指出这些画不仅差劲,还丑化苏联工业。‘这跟烟筒有什么关系?画家画这个城市时,为了加强印象,有权多画几根烟筒。’我顶撞道。‘你们这样看,可我们认为他无权这样画。’苏斯洛夫继续说。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同我的辩论感到厌倦,便走进隔壁的一个展厅,那里陈列着涅伊兹韦斯内(赫鲁晓夫墓像的塑造者)的雕塑作品。涅伊兹韦斯内回忆道:‘赫鲁晓夫对我吼叫起来,说我白白浪费人民的钱,塑造出来一堆大粪,我则指责他对艺术一窍不通。辩论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他受人挑唆,陷入可笑的处境,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员,不是评论家,缺乏应有的美学知识……我对他说,这种挑唆不仅针对知识分子和自由化,还针对他本人……”(《各民族友谊》)画家没提到站在他们旁边的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却记住了他。1976年涅伊兹韦斯内申请出国,安德罗波夫已经允许了,但他仍无法出国,因为苏斯洛夫反对,苏斯洛夫要把他在国内折磨死。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3)
苏斯洛夫一贯仇视《新世界》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反对个人迷信,呼唤民主和自由,它的主编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思想活跃,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的方针,发表大量揭发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作品,要求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同那些粉饰生活的作品做坚决的斗争。《新世界》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激进、渴望改革的作家,形成进步知识分子的营垒。而这正是苏斯洛夫所不能容忍的。苏斯洛夫是斯大林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同极权体制熔铸在一起。他迷醉于陈腐的教条,不接受任何鲜活的思想。他早想把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脚踢开,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非等闲之辈,是苏联有影响的诗人,在知识分子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无法轻易免除他主编的职务。苏斯洛夫对《新世界》采取全面围剿的策略。《星火》杂志发表《十一人的来信》,猛烈批评《新世界》给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真理报》等大报发表建筑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们致编辑部的信,谴责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转述西蒙诺夫的话,不久前杰米切夫(党中央书记)在列宁格勒讲过一次话。他回答提问中的两个问题:‘你们准备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我们同他斗争,抵消他的影响。’另一个问题:‘你们如何对待《新世界》?’‘这件事比较棘手’,杰米切夫回答道,‘首先,著名作家、作协第一书记费定是编委;其次,这个杂志有个特点:善于发现天才。’‘第三呢’,特瓦尔多夫斯基笑着说,‘我这样理解,让他们给我们发现更多天才,如果少了,我们就取缔他们。’”(孔德拉托维奇:《〈新世界〉日志》)接着又采取组织措施:1966年解除了编委扎克斯和杰缅季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同苏斯洛夫争吵了二十分钟,拒绝工作,抗议不经主编同意便撤换编委,而苏斯洛夫用党的纪律威胁他,叫他必须留任。”1970年,作协书记处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加强《新世界》编委会的决议,解除孔德拉托维奇、拉克申、维诺格拉多夫、马利亚莫夫和萨茨(即《新世界》的全部老编委)的职务,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孤掌难鸣,被迫辞去主编职务。苏斯洛夫却劝特瓦尔多夫斯基正确对待人事变动,相信党中央。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1)
1946年,苏斯洛夫进入权力中心——苏共中央委员会,担任书记处书记。1952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被选入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中还设立有常务委员会),成为二十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这当然是斯大林的意思。但斯大林死后,主席团缩小为常务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政治局,他没能进入,但仍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48年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成为党内头号理论家。1949年初至1951年,他曾担任《真理报》主编。1989年我在苏联执教时,民间流传着两句话:《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除没真理和没消息外,还没意思,连尚能吸引读者的游记一类的文章也没有了。第一版通常刊登各行业和各民族向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致敬信或汇报提纲,今天的和昨天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今天是建筑工人,明天是集体农庄庄员,后天是哈萨克族,大后天是乌兹别克族。其次便是打棍子。不是批评哲学权威德波林,便是抨击语言学泰斗马尔,还主导打击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真理报》上最活跃的是米丁、尤金等小丑。另外便是赞扬《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类影片,夸奖《从小爱护荣誉》、《金星英雄》等小说。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不仅灰色,而且凶残。斯大林死后,他并未积极参加权力斗争,因为自知没有资本。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合并为主席团,人数大大减少,苏斯洛夫成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遭到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激烈反对,支持赫鲁晓夫的是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洛夫等人。苏斯洛夫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静观事态发展。莫洛托夫等人终于顶不住了,转而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大会结束的那天做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莫洛托夫等人支持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权宜之计,先保住地位,然后伺机反扑。一年后,1957年6月18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莫洛托夫提出解除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的建议,赫鲁晓夫当然坚决反对,但主席团大多数人赞同莫洛托夫的建议,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寡不敌众,急需新的盟友。米高扬找刚从外地赶回来的苏斯洛夫,说服他支持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知道马林科夫是自己的对头,如果他上台,对自己凶多吉少。他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比同马林科夫等人的关系亲近。他早在工业学院教政治经济学时,赫鲁晓夫是学院党委书记,两人就有交往。苏斯洛夫从自身利益着想,决定下一次赌注,支持赫鲁晓夫,尽管他的思想体系更接近莫洛托夫等人。赫鲁晓夫最终战胜莫洛托夫等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并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苏斯洛夫也成为胜利的一方。赫鲁晓夫改革的步子越迈越大,同苏斯洛夫时常发生冲突,并开始疏远他。苏斯洛夫为保存自己的权势,减慢赫鲁晓夫的步伐,甚至促使他走回头路,制造了“练马场事件”。苏斯洛夫想让赫鲁晓夫看看改革的后果。此后,赫鲁晓夫虽向斯大林体制倒退,但仍不重用苏斯洛夫,让他负责协调与兄弟党的关系。1964年10月召开中央全会,逼迫赫鲁晓夫退休。会上,由苏斯洛夫作报告,历数赫鲁晓夫执政十一年的错误。但苏斯洛夫并不是倒赫的核心,他是最后才知道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倒赫的阴谋的。他听了吓坏了,嘴唇发青,浑身哆嗦,只低声说了一句:“你们想干什么呀?会爆发内战的。”报告不是他写的,但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两人都不肯念,主席团最老的成员米高扬始终是赫鲁晓夫的盟友,当然不会念,只好轮到苏斯洛夫念了。苏斯洛夫哆哆嗦嗦,匆匆忙忙念完,“十月政变”便成功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斯洛夫才真正成为苏共的第二把手、控制意识形态的凶神恶煞。把作家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剥夺了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院士劳动英雄称号并把他流放到高尔基市,审判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封杀《新世界》杂志,等等,等等,都是他干的。他为了控制舆论,把头脑僵化、不学无术、听命于他的人安排在宣传阵地的关键岗位,如任命柯切托夫担任《文学报》主编便是一例。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也干了不少坏事。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苏斯洛夫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2)
苏斯洛夫是一生没写过一本书的理论家(他的《三卷集》里的文章和演讲辞都是别人捉刀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宣传陈腐的教条和扼杀鲜活的思想上。他这样做很难说是出于信仰,因为他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我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他甚至没系统地读过马恩的著作。他是极权体制的产物,是它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它的守护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个人已经获得的权势。如果形势发生骤变,他这个只会摘引列宁和斯大林语录的人,很难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如果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以他的水平和能力,充其量当个不受学生欢迎的中学老师。换句话,没有极权主义,就没有他的一切。国家和人民从不在他视野之内。1974年,别柳金画室的一百名画家联名致函苏斯洛夫,要求他下台。信很长,我只摘译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这在艺术中还不是最可怕的。艺术像河流,无论您的堤坝,无论您如何想方设法让河水倒流入你们用查禁和摧毁设置的钢筋水泥的河床,都无法阻止河水的奔流。最可怕的是,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剥夺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把他们变成执行您荒谬而残酷的意愿的机器人。您的宗旨是使俄罗斯文化粗浅化,宣传极端贫乏的理想,否定苏联人精神兴趣的复杂性。您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使苏联各族人民变得蒙昧,以便您制造毁坏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一切规律的土壤。
苏斯洛夫1982年去世,死在勃列日涅夫前头,死得其时。勃列日涅夫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都是中央和各地的党政官员,至于普通知识分子,恐怕没有人去,要去,也是被迫的。
(原载《收获》2003年第4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1)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解放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被译成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