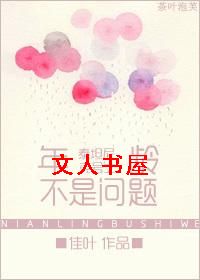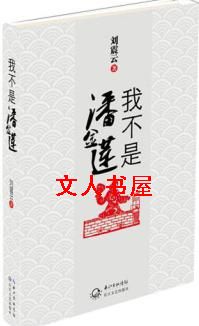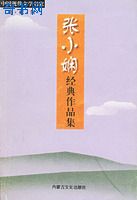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吓得立即停住了脚步。但手中还是不停地对着总理的背影又拍了两张。第二天,我放出照片以后,拿给同学和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们看,大家都说我的照片比新华社记者拍得棒。有人还拿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把那头版头条的大照片和我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9)
后来,我还在“十一”国庆节的夜晚,在天安门广场拍了放礼花的照片,也挺漂亮的。我自认为是个当摄影记者的料,没想到12年以后,我还真的当上了国家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不过,我12年后的摄影观念与当年已经大不一样了。
大约在夏天,我莫名其妙就被大家推选当了班里“复课闹革命”的领导成员。其实,我只是帮着跑跑龙套。
我们组织过对原班主任的批判会。我们高三的同学已经20岁了,不会像低年级同学那样动粗。虽然我们开会前还仔细准备了提纲,但是,会还是开得时断时续。冷场时,有同学猛敲惊堂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有一个叫刘建南的同学,他是我们班上长得最帅的,高鼻梁、大眼睛、白皮肤,像个外国人。他的父母都是老教师。“###”前,他每次到我家,一进门,见我父亲就是一个直角的大鞠躬,大声叫:“伯父好!”然后又对着我母亲一个大鞠躬,叫:“伯母好!”在大院里,我们都管长辈叫叔叔阿姨的,我妈就说,“哎呀,这孩子真懂礼貌。”我们俩还一起练过双杠、单杠和在沙坑里练前空翻。有一次,我还被摔成了“椎间盘突出”,是我们班长侯红军找到一个酱油厂的工人免费帮我捏好的。刘建南有个绝招——吹口哨,苏联歌曲吹得特别好听。他吹口哨时嘴不动,有一次我们上公共汽车,他吹起了口哨,车上的人都不知是从谁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看着大家东张西望地寻找声源,他仍得意洋洋地吹。
可能是大家看刘建南比较自由化一点,还是他惹了什么事,我也忘了,反正班里开了一次“帮助”他的会。这天大家用课桌围成一圈,刘建南坐在中间,说着说着他把椅子往后一靠,跷起二郎腿,嘴里蹦出一句:“×,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
批判会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后来,当大家开始找工作了,同学们互相告别时,大家不无感触地说:“还是刘建南说得对,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如今又过了40年,我更觉得世间没有一个大傻B,就像世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样。当然也有人不时犯傻,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权力过剩、金钱过剩的过儿。
在地坛学拳练剑
虽然我妈是“摘帽右派”,我爸也因“右倾”被降职使用,而且他们翻案的大字报就堂堂正正地贴在侨委大院里和王大人胡同的墙上,但在“###”时不论哪一派的群众都对我爸妈比较同情,没人来抄我们家。也有可能是我家三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我20岁、安弟17岁、安末15岁),又都学过武术,家里还有气枪,没人敢来抄我们的家。所以“###”对我们来说,还算是比较悠闲平静的。没事时,我就在家里吹笛子,吹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我最喜欢吹的是《长征组歌》。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0)
印象中我们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一般不参与大人们(哪怕是爹妈们)之间的###。我们60号大院里的男孩子算起来有20多个,小的才七八岁,就我最大。比我大的都是大学生或者有工作单位了。我们中学生和小学生整天都无所事事,就寻思着哪里有好玩的。一天,叶德阳说地坛有一个姓马的老师傅正在收徒弟、教武术。我们一大帮孩子听了很感兴趣,我马上决定带着大点的孩子去地坛见见这个马老先生。
我们一帮人前呼后拥地来到地坛,请马老师收我们为徒弟。结果我们七八个比较大的孩子都报了名,学费是每人每月一元。
那时地坛有很多场子,有练形意拳的,有练八卦掌的,有练太极拳的,也有练长拳的,还有舞剑的,但是经政府注册可以收费授徒的场子并不多。马老师的场子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后来听说他原本是国民党南京监狱的典狱长,是太极拳界有名的拳师。
马老师叫马月清,约有六七十岁,身材高大,对学生很和气,很懂得因材施教。安弟那时身体不太好,马老师就教他练太极拳,而我已经有很好的武术功底,马老师就教我学一路查拳、二路查拳,一共学了四路查拳。每天早上和下午我们要去两次,一开始练踢腿、下腰、压腿、走台步、打旋风脚,然后学拳。马老师比我当年跟的陈子江老师教学的进度快,但现在想来,跟陈老师学的八极拳基本功很扎实。而马老师是按体委教材教的,主要在于活动筋骨,练习功架。没想到这些工夫却为我后来在西双版纳农场的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打下了基础。
我学了几套查拳之后,马老师又教我舞剑。不久,我的剑就舞得像模像样了,把那长长的剑穗舞得上下翻飞。后来马老师又教我练棍,我就去土产商店买了一根白蜡树干做的木棍,白蜡棍齐眉高,直径有一寸左右。没过多久,我就能把棍舞得嗡嗡响。后来安弟告诉我,有一次我没在,马老师教训其他弟子说:“你看人家安哥,在地坛东头打旋风脚,地坛西头都能听得见!”应该说,在马老师的众多新老弟子中,我是很受他老人家器重的。
马老师的场子就这样很是红火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午,马老师说有一个从南方来的拳师,要跟他学两招。“学两招”在行内就是江湖上所谓“比武”或“踢场子的”。那人先给了马老师五元,当是学费,然后他们就来到一片树林里。马老师一上手,就把他“发”出去老远。那人甘拜下风,于是双手抱拳、鞠个躬就走了。
1967年,地坛是个很清净的地方。每天早上,树林里、围墙边,有咦咿呀呀吊嗓子的。练八卦掌的大爷###了膀子,站个骑马蹲裆式,抡着胳膊把###拍得“啪——啪——啪”地响,一旦脸上汗水多了,就用双手从大光头的后脑勺往前捋过脸上,似乎用汗水抹脸可以养颜。有时候他们还用前臂去撞树,撞得树干“砰——砰”地响。我曾学着撞了几下,撞得胳膊生疼。还有练形意拳的,他们把平地趟出了直径三米左右的圆的沟;练太极推手的相对而立,四臂相绕像车轮似的转,时疾时徐地“较劲儿”。马老师和贺老头就经常练推手。我们马老师的学生排着队,“唰——唰”地踢腿…… 。 想看书来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1)
那时候,政府不许武术老师教技击,所以在那一年的“逍遥”练武的日子里,我没能学得什么防身的绝招,此后打架我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我的人生岁月中,我不仅养成了不时活动活动拳脚的习惯,而且还在我的心灵里,保持了一片清净之地。这可能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在地坛,我们还交了一个朋友,他姓李,是个说河北方言的壮汉。他打的拳很短、很难看,但那套拳却拙而有力。我们院儿的小孩也跟他学了一套拳,叫子母拳。当时和我们一起向老李学拳的还有一位中央乐团的提琴手王学志。
老李跟我们讲,在他们河北雄县老家,以前每村都请一个拳师带全村的小孩练武,同时还学唱武戏,所以,他们十八般武艺都会。平时就可以看家护院,逢年过节就能上台唱戏。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河北的年轻人以前人人会武术,所以抗战的时候,他们那里的地道战、地雷战才打得那么棒。
老李还会耍枪。他说,前不久他们厂子里武斗,他抄起棍子从一大帮人中杀出重围。听他讲述,我总是充满好奇,却丝毫没有想参与的欲望,正如我后来做了记者一样。这辈子我都是好奇的旁观者。我只是希望在自己的手上,有样看家的“玩艺儿”。
那时候在北京住楼房的还不多,我们60号大院外有一帮前永康胡同的孩子可能是看我们的楼不顺眼,经常悄悄地来砸我们的奶瓶子,甚至扔石头砸我们的玻璃窗。
有一天,这帮孩子又来挑衅。冲在前边的孩子手里还抓着两块砖头,我便冲了过去,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我顺着他往上挣的劲,往上一提、脚下一踢。他便飞了起来,仰面朝天摔在地下。我这才知道,刚才下意识的动作是平常练太极推手的效果。只见他爬起来带着他们的人,边走边骂骂咧咧地说:“XXXX!今儿晚上你们等着瞧!”
我知道这帮孩子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的头儿我也认识,是个比我大一些的小伙子,他白天上班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晚上能叫来多少人,于是,我就回学校跟班里的同学说:今天晚上有人要跟我们院儿打架。那时我们班的同学不论什么家庭出身的,都很团结。结果那天晚上,我们班的同学只要家住得近的全来了,有一二十个呢。连那位曾因为骂我的好朋友王开平“狗崽子”,我跟他对骂的同学也来了。
这天傍晚,我妈从饭堂打来两盆包子,慰劳我的同学们。
天黑以后,刘安阳就翻墙出去侦察胡同里的情况,我让院里的小孩子在各个阳台上准备了石头,大点的分别埋伏在灰楼和黄楼的楼梯口和煤堆的后边。我站在院子中间,提着一根白蜡棍等着,要跟他们决战。可是,始终没见动静,等到十点来钟,他们还没来。可能他们发现我们来了很多人而畏缩了吧。正好我们同学中有人带来北京市的治安布告,我们就到对面的胡同里贴。后来还认出一两个孩子来,我们把他们拉出来警告了一顿。以后他们再也没敢来惹事儿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2)
那天晚上,院里的大人都没出面。
美景中潜伏着危险
有一次,听说上方山云水洞很好玩,最近有五中的红卫兵去爬山时还摔死了人,我的小学同学侯克平为救人还摔伤了。我们60号大院的孩子们就决定也骑车去玩。
上方山离我们家有一百公里左右。半夜三更我们就骑车出发了。天亮以后,看见公路旁边的山上全是梨树林,结了很多梨子,周围也见不到人,我们就高兴地摘了很多。没想到,没一会儿工夫,树林周围便冲出来了好几个气势汹汹的农民。结果我们赔了几块钱,便背着一袋梨子上路了。
到了上方山入口处,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沿河滩走进去,出现一条小路,走着走着,就全是鹅卵石了,推着车很难走。我们就把车存在山村的老乡家,继续沿河往山里走。不久,在河滩旁见到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直径有十来米,那水是显得诡异的深蓝色。走到云水洞山脚下,见到有阶梯上山,阶梯很陡,大家又很累了,干脆我们就在河里洗澡,然后吃了些带来的干粮,又躺在大树荫下的石头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爬山到半山腰,只见山上有座寺庙,庙里却没有和尚,佛经扔得到处都是,拣起来看,里面画着很多佛教故事的画,看样子像有人来破过“四旧”。我们在庙里遇到几个管山的人,他们给指了路,我们就直奔云水洞而去。据管山的人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外国探险家进去考察过,其中有一个探险家就死在里面了。
云水洞口有一道天然的石屏风,绕过屏风只见那洞口还真的飘着薄薄的白云,洞口有一人多高,人一走过去那白云就散得无影无踪了。越往里边走,洞越窄,拐个弯儿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打开手电筒。一路往前走,来到一个很窄的岩缝,只能一人侧身钻进去。走了十来米,面前豁然开朗,是方圆一两亩的很高很大的黑色大厅,拿四节电池的手电筒往上照也很难见到顶。洞里回声很大,很渗人,四周全是黑色的石笋。以前可能有人拿火把照明,熏得到处黑黑的,手一扶石壁或钟乳石,就变成黑爪子了。据说,抗战的时候,这里曾住过很多躲避战乱的老百姓。想必他们当年都是点火把照明的。继续往前走,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很窄的小洞口,我们鱼贯摸索前行。又是豁然开朗,来到了另一个大厅。我们连续走过四五个大厅,最后走到一个长满钟乳石的坡,像个漏斗似的,坡面很湿滑,坡下面是一个只有人的腰围那么粗的小洞。我们看着觉得有点害怕,没人敢下去,就折回来了。后来听说,死去的外国探险家就是从那里下去回不来的。
出了云水洞,我们又去侯克平救人的地方。绕过山梁有个瀑布,走到瀑布上面的小潭,潭水很绿,潭的外延有水漫出跌下深渊,形成瀑布。水潭的边沿生着绿苔,很滑很滑的。据说有个女孩子就是从那儿滑下去的,她男朋友去
![[进击的巨人]才不是萝莉控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3/3006.jpg)
![[火影]悲剧不是你想悲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3/302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