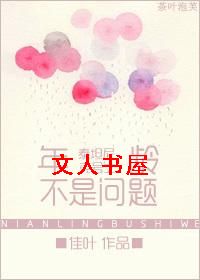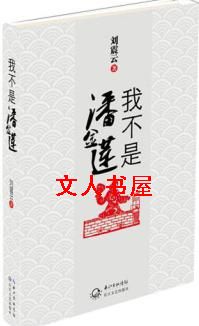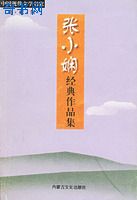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历史中的小牛皮(1)
颜长江
前几天看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心里比较有感触。一个小娃娃,拒绝长大,永远挂个铁皮鼓,不高兴了就敲一敲。历史的鼓点儿是正步、是坦克、是大炮,“历史”响几声,他鼓槌就敲几敲。他还辅以一绝活儿,就是高声###,能让玻璃制品闻声而碎。就这两样,撑了一辈子。他也不怎么说话,就这么表达。
咱们敲什么?敲快门儿。
安哥敲了一辈子快门儿。他的照片是国际级的,我打小就以他为偶像。后来竟认识他了,才知他还有另外一绝活儿,就是吹牛皮。我是他最忠实的听众之一,因为常在一块儿吃饭,有些故事我都能替他吹了。他总是温和、细致地娓娓“吹”来,一吹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岔路比较多点儿,吹着吹着自己也找不着北了。他吹得很顺,但吹到纸面上就挺慢的,一篇千字文会折腾一星期,变成蜗牛了。但照样很精彩,比如《从前有座山》是摄影界一代名文了。他吹得真诚嘛。
我把安哥和那袖珍人联系起来说,也许有点不合适。因为安哥形象很好,他头一号爱吹的,就是他小时候特美丽,还选上了秀,给胡志明献花。我想起《铁皮鼓》纯属字面上的联想,都是皮吧。细想一看,安哥的两项绝活就是铁和皮。相机是铁的——硬的,说话是“皮”的——软的,一硬一软。
事情就怕想,再想一想,安哥也是经历了大历史的人,整个新中国。经历下来还活得开心,没两项绝活儿不行。和那小娃娃一样,安哥也经历了一个比较荒诞的时期,他的青春与“###”搞在一起。当然,我们虽经历十年变局,但还是比“二战”和平得多,所以,安哥的牛皮不是###型,而是比较可爱甚至貌似柔软。都挺合适的。安哥的青春故事,是本书吹得最精彩的,总让人想起姜文两部杰出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就是那种明晃晃地超现实的感觉。当然情节不同,安哥的农场故事可能更精彩,比如他们在热带雨林里打着红旗批斗###的场景:
“……前景是站在河中的傣族男青年那刺满佛教文身的###背影;中景是勐龙桥上我们那荒唐的###队伍;在桥那边,河里蹲着一排正在方便的傣族姑娘,像一群浮水的小鸭子,她们也面向着勐龙桥望着我们;背景是美丽的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
安哥当时置身队伍之中,但没有相机去拍下来。他只能回忆这一幅画面。这是一幅本应庄严然而却荒谬的画面。革命队伍庄严,###与自然优美,但当队伍遭遇后者时,就不知道谁革谁的命了。庄严变得荒谬,柔美的事物才真是庄严。如同崔健描述情侣###的词句:“那心中的火那身上的汗,才是真的太阳真的泉水呀!”
没拍下来,但安哥的叙述极有画面感。他就是干这个的。另一个画面是在庐山之下。那时节安哥的父母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边的农场里。他当时是西双版纳知青农场宣传队的角儿,请了探亲假千里迢迢去江西看父母。傍晚,暗下来的天空成为安哥的幕布,在打谷场上,他让父母坐在小板凳上,他又唱又跳,为双亲来了一场专场演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历史中的小牛皮(2)
这一幕“渔舟唱晚踏歌图”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的想象中,庐山也出现在这幅画面里。他爸爸妈妈看着成年儿子跳舞时,是否比当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畅快呢?
安哥的这些个故事,其幽默感、戏剧性是不消说的,更重要的是其感人之深,发人深思。他的牛皮已吹到当代艺术的程度,较其摄影更能表达现实中的超现实,非常的前卫。有时我想,姜文要是把安哥的故事拍成电影,那就精彩了。因为,安哥的牛皮真不是吹出来的。他活得精彩,不仅因为他悲喜交集的角色天分,而且因为他同那个小娃娃一样,莫名其妙地总是处于历史的中心或主线上:
童年、少年,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父亲有地位,是受命缝制第一面国旗的人。安哥是“红旗下的蛋”,在最红的红心中孵化成长;青年,是“老三届”的老大,南下西双版纳,置身知青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壮年,南下广州工作定居,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
在这条线上,直接或间接,他比常人更多地见识了一些不一般的人物。有的出于偶然,比如他吹的“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演出完了,陈凯歌是来蹭饭的”;更多的是长期的朋友,比如侯德健和刘索拉。有一点我很惊奇,就是安哥讲述这些有名朋友的时候,不仅没有任何夸耀,而是完全把他们当作渔民、工仔一样的朋友来叙说,甚或只说他们普通的一面。安哥很本真天然,没有分别之心。他只有一颗童心饶有兴趣地看着历史主线上的一切有趣之处。
所以,安哥的牛皮其实不是吹的,而是客观的记忆。他的记忆就是一面“童心宝鉴”。在这宝镜之前,一切都相对接近原形,所以可视为“信史”。又扯到史了。自法国布罗代尔等人创立年鉴学派史学以来,大家都开始相信,日常生活的状态更接近历史的本质。那么,安哥吹出的日常和他拍摄的日常,可能是很不寻常的。尤其是安哥虽然嬉皮笑脸一些,但他暗藏着相当的历史感。由于经历与职业,他不得不用相机和幽默去应对历史和生活。我为此写过《在沉甸甸的历史面前滑不溜手》,就是写他用相机和琐事与历史“周旋”的人生本质。他的摄影和故事都是一样的风格:作为个人,我在严酷现实面前带点儿狡黠,但你这对手别想轻易溜走!现在总结起来,这可以叫“牛皮精神”,牛皮有韧劲,煮不烂扯不断,又相当灵活,反戈一击时还可以套住你。安哥要出本“牛皮书”了,这叫做“我要抓住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报应到了。
总不能老叫历史欺负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应对方法。小娃娃是敲铁皮鼓,阿Q是搞自我心理治疗,《活着》的主人公是皮影戏,我爸爸是吟几句旧体诗,我一位姨夫是独自拉二胡。安哥更好一些,到了这年头,他的摄影和琐事竟可以有“话语权”了,整得出来,还可以安慰别人。哥哥不是吹牛皮,一吹就吹出一本史记。
安哥和他原生态的故事
吴东峰
这是一个人和一本图文书的故事,也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更是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故事。
2001年8月,一本名为《生活在###时代》的图文书在全国各地热销。许多人从这本书中惊讶地发现,以往对南方的改革开放的印象大多汇集在这里。
略显苍老而又尴尬的大龄青年集体婚礼中的新人们,高第街上含羞而胆怯的女服装个体户,挂着###像的普通农家,正在简陋教室里走“猫步”的选美女郎,穿着拖鞋带着孩子上班的第一代洗脚上田的女工……
面对着作者1976—2000年25年间的700余幅摄影作品,这时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那一幅幅曾经司空见惯而又触手可及的普通生活画面竟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逝去了的时代记忆。
作者在这本图文书里捕捉到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物,一个个动作,一个个表情,而是一个时代的丰富信息,是###时代的民间众生相。它亲切地告诉我们:历史的巨变就在我们身边发生!
不仅如此。这本图文书,还使“###时代”这一词组不胫而走,成为全社会自发的公用名词。“###”三个字的意义超越了个人和政党的狭义局限,真实而形象地成为人民大众生活富裕起来的精神象征,比如当年之《东方红》与毛泽东一样。
从此,这位一举成名的摄影者——安哥的名字写进入中国现代摄影史。
也正是这本图文书,使我认识了这位中国南方摄影圈里的“大哥大”。
记得是2005年上半年,我们准备请广州的一些知名作家动笔,出一套关于改革开放时代纪实性系列丛书。对于这套丛书的策划,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不应景不解读,大历史大文化,更自由更真实。
一次偶然的机会,《羊城晚报》的资深编辑陈朝旋向我推荐了该报的摄影部主任颜长江。颜长江在涉足摄影圈前已出版过两本书。他的摄影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穿透力,他的文字轻松而凝重,单纯而深刻,这些我早有所知。由他来写这样的书,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可惜由于其他原因,长江先生没有加盟这套丛书的写作,但他却向我们郑重而热情地推荐了安哥。他对我说:“安哥虽然不是作家,但他出过一本图文书叫《生活在###时代》。 你们可以先看看!”
读着《生活在###时代》里一幅幅照片,我不禁怦然心动。其实,这里面的许多照片我不止读过一次,每次读它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有时激动得难以掩卷。更使我惊讶的是,这里没有伟人的决策,惊人的内幕,激烈的交锋,宏伟的场景,但却真真切切地见证了那个时代翻天覆地的深刻巨变。
安哥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拍出这么多极为普通而又极具时代意义的照片?他是怎么想到要拍这些照片的?这些照片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是时代赋予的机遇还是人生经历的必然?一位普通的摄影者为什么会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于是,我们请安哥给我们讲故事,他讲的故事虽然零碎而不完整,粗糙而不精致,有点鸡毛蒜皮和啰嗦唠叨,也并不那么艺术化和文学化,但正是这种原生态的故事,以其淳朴自然,以其真实生动,以其并非想象的传奇、情景、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打动了我们。
安哥以他那略显疲惫而仍闪烁着纯真的神态,以他那执拗的人本立场和尚未完全褪尽的“贵族”气质,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诉说了属于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故事,也属于这个时代的因果相袭的故事。
人生是时代的折射,一个时代的来临并非偶然。摄影是时间的瞬间,一个瞬间的成功也并非偶然。
是安哥拍出了###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了安哥?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在安哥的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中去追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1)
“哥哥不是吹牛皮”这话本来是四川小知青摆龙门阵时的口头禅,他们的原话是“哥哥牛皮不是吹哩”,像是唱歌一样,“索索哆哆发索拉西——”。想必是在四川的茶馆书场里,说书人话音刚落,半拍之后,惊堂木就会响起,给整个乐句加上一个高音“哆”,和一个完美的休止符。近年来,这句话在不知不觉间也成了我的口头禅。
不知不觉我今年已经62岁了,我们这一拨是最后一批“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了。人们都说人越老,对往事记得越清楚。我讲的这些“过去的事情”真的不是吹牛皮。不过,在我们云南西双版纳,“吹牛”的意思也不光是说大话,它还含有北京话“侃大山”的意思。我是搞纪实摄影的,平时就讲究一个“真”字。回想当年虽如梦似幻,却都是真实的经历。这么多跌宕起伏的时代际遇,这么多像坐过山车一样揪心的人间悲喜剧,咋就都让咱碰上了呢。
小时候,大人都叫我安哥,让我觉得特占便宜。如今,20多岁的新闻、摄影界同行朋友也都叫我安哥,让年逾花甲的我仍觉得年轻,心里也很受用。不过,用广东话说,我这就叫做:“大不透。”常有同行小朋友问我:“安哥这名字真好听,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我的小名就叫安哥,我的曾用名叫彭安哥。我两个弟弟叫安弟和安末。现在,安哥成了我的笔名了,我身份证的名字叫彭振戈。
1957年我曾代表“祖国的花朵”给来华访问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献过花。本来,我还有可能被选上在国庆节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的。可是,第二年,我的爸爸和妈妈被打成“右倾”和“右派”,被送去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劳动改造。于是,我11岁就成了一家之长,饱尝社会的炎凉。
上中学的时候,我一直到18岁上高二了还入不了共青团,理由十分充分:就是因为没有和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三反分子”的“摘帽右派”的母亲划清界限。于是在全国学雷锋和学清洁工时传祥的运动中,我利用节假日和寒暑假到东城区的清洁队参加了五十多次掏粪劳动,每次一干就是八个小时。哥哥不是吹牛皮,北京东城区几乎所有的胡同,我都曾背着粪桶去掏过大粪。
1966年8月和10月,“###”初起的时候,我分别和两拨同学以“大串联”的名义游历了全国十来个省的城市和山河。在去内蒙古、甘肃、新疆、陕西和
![[进击的巨人]才不是萝莉控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3/3006.jpg)
![[火影]悲剧不是你想悲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3/302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