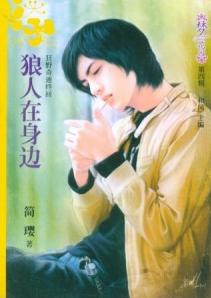人在胡同第几槐-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从抖腿到凝神
我小时候绝非神童而是顽童。四五岁的时候,在重庆,父母常带我和兄姊去看厉家班的京剧。厉家班是抗日战争时期陪都最出色的戏班。“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并坐观赏过厉家班的演出。但那时侯我看不懂京剧,在哐哐哐的锣鼓声中,坐在大人膝上,兴奋莫名而已。八岁时随父母到了北京,新中国有了新剧场和新式演出。有趣的是,父母都很适应京剧的新式台风,我却偏冥顽不灵。有回他们带我去看戏,我在座位上扭股糖似的不安生,哼哼唧唧地无理取闹:“我要看茶壶嘛!怎么老没茶壶嘛!”原来旧式京剧演出,主要演员唱完一段或数段,就会有一位穿长衫的人端着一个小茶壶,出来喂歇气的演员饮茶润喉,行话叫“饮场”。虽说京剧是大写意的虚拟手法,但“饮场”毕竟破坏了剧情的连贯,而且,你想想,无论是即将碰碑的杨继业,还是带枷发配路上的苏三,观众正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却忽然一段唱完有人来给他们喂茶,如此享受,作何解释?除了“饮场”,旧时还有“检场”,比如《三堂会审》,苏三跪下前会有穿长衫的人来为她放下软垫,终于唱完站起来后那人又会出来取走那个软垫。我小哥很早就是票友,攻梅派青衣,他在家里自排《三堂会审》,我就总盼着当“检场”的给他放椅垫,后来他很不耐烦,翘起右手食指“嘟”地一声将我斥退。
看京剧,起初我只爱看三种剧目。一种是开打的,《三岔口》那种“冷打”不甚喜欢,最喜欢的是锣鼓喧天中满台扎靠背旗摆翎的武生花面,耍着大刀斧钺双锤双锏,激战得不亦乐乎,而且当中还一定穿插许多小兵的筋斗连翻,每当锣鼓顿止,台上诸战将凛然定格亮相,我也会和大人内行一样使劲鼓掌。第二种是旦角戏,但《武家坡》那种青衫贫相的旦角不懂得欣赏;《贵妃醉酒》那样的宫妆又觉得累赘;最喜欢的是《凤还巢》里程雪娥那类的装扮,头上许多饰物在灯光下闪烁如星,更有那衣衫上绣出的大朵牡丹或七彩珍禽艳丽夺目,如有这样的“阿姨”(刚到北京还不习惯使用“阿姨”一词)贯穿全出,则剧情已在其次,小小的心,完全被其华光异彩所迷惑。第三种是剧情层次分明的“整戏”,如《三打祝家庄》,有悬念,有跌宕,小孩子也能看得明白。
十来岁的时候,跟家长去看戏,大体上坐得住了,但如果是沉闷的折子戏,前后剧情不明,只有一个衣衫素净的老旦或老生在台上咿咿呀呀许久,我不耐烦,不由得左腿便连续抖动,母亲一般总坐在我左边,她就会眼睛盯住台上,右手默默地按住我的左腿,或者更轻拍几下,以示制止,有一回我仍顽固地抖腿,她忍不住侧过头来,轻声责备:“幺幺,不可以!”那时的剧场基本上都是铁木结合的连体椅,我的抖动,使附近坐席上的观众也感觉到了,妨碍他们静心赏戏。记得那回观戏到家,父母跟我郑重地讲了一番道理,大意是无论看得懂看不懂,要尊重演员的演出和同场观赏的人士,而且,艺术这个东西,你以一份虔诚的尊重进入,久而久之,原来不知其味,渐渐可以品出醇厚的美味。在父母兄姊的指点带动下,我不但逐渐改掉了在剧场里抖腿的臭毛病,像边看边吃零食呀,非把没喝完的汽水带回座位、一不留神把搁在脚下的瓶子碰倒滚动咣当当响呀,没到半场休息就非要挤出大半排去如厕呀,等等行为也都逐渐克服。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以欣赏京剧来说,我算得上基本入门了。像老旦戏《傅氏发配》、骐派老生戏《徐策跑城》。场面并不华美热闹而心理冲突细腻复杂的《二堂舍子》等我都能凝神观赏、品出味道了。
现在影视网络文化发达,像在露天或体育馆里举办的歌星大型演唱会,我也将其划入此类视听文化的范畴,古典意义上的剧场演出,相对式微,京剧和其他戏曲都不够景气,连“大剧场话剧”也比较萧条,“小剧场话剧”虽然活跃却又“星火”难以“燎原”,倒是音乐会和芭蕾舞等品种较为热络。但以我身临现场的感受,总难获得一个“虔诚尊重”的欣赏氛围,不管演出前怎样广播提醒,演出时总有手机彩铃声响起、闪光灯明灭;有的年轻恋人是观赏为次欢聚为主;或演出间进进出出,零食不断;或坐席上姿态做派不雅;有的年轻父母望子女成龙成凤,却又不会教育指点,台上音乐偶像献艺,台下幼龙雏凤比抖腿还要嬉皮。
愿以母亲留下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并供大家参考:要像爱惜每一篇字纸一样,珍惜这辈子亲眼看到的每一场演出。
。 想看书来
找不同
那天从城里书房绿叶居去往农村书房温榆斋。到了温榆斋门口才发现忘带开门钥匙,只好再返回城里。轮换在两处书房里活动,已有八年之久,忘带开门钥匙却是头一遭。难道我已成了一个“恍惚的人”?
《恍惚的人》是一本小说的书名,作者是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这本小说在“*”后期作为“内部参考读物”在中国翻译出版。当时译介它,是认为内容具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老人尴尬处境的进步意义。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出版社将其正式发行,被当时如饥似渴地扑向外国文学的读者们飞快购尽,于是加印几次,达到很大的一个印数。我那时读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冷静的写实工力,有一个细节,写冬日老人来不及入厕失禁,在廊檐下往雪地里尿出一串“冒号”。说它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老人的冷漠,当然是一种解读,但作者其实是透过老人题材,写人性,探讨生老病死这一永恒的主题。花无百日红,人有衰老时,未老者如何对待老者?老者如何面对自己?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课题。“恍惚的人”需要在夕阳箫鼓里有尊严地默默燃尽生命最后的光焰。
一九八一年,我参加三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赴日访问,在东京见到了《恍惚的人》的作者有吉佐和子,她是一个带男相的妇人,而且做派也很有点中国古代梁山好汉的气概,她和我们代表团长杜宣是老相识,知道杜宣在“*”中吃了苦头,见杜宣那天腕上无手表,当即抹下自己腕上的一块高档手表,让杜宣戴上。她说话直来直去,听说《恍惚的人》中译本印数已达十万册,我们本来以为她会高兴,没想到她板起脸问:“谁让你们印那么多的?”竟然生起气来。从那一天起,我算知道了他们那边的文化,和我们这边文化的一大不同,就是雅文化包括纯文学和俗文化,包括畅销书,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虽然二者也有交汇融合的部分,好比两个各有圆心的大圆边缘互割,形成一处暧昧的“叶子瓣”区域。但两个大圆那“叶子瓣”区域外的广大部分,是互不相干的。有吉佐和子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她写的书拥有一个固定的读者群,出版她的书的机构绝不会亏本,她当然也能获得不菲的版税,过着尊严的小康生活,但她不是畅销书作家,一听说把她的书印得那么多,她本能地觉得不对头,认为是给她错定了位,有违她的美学追求。当然我们赶忙给她解释,中国人口那么多,十万册的印数其实并不算很多,当时重印了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一刷的册数就要多许多。这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日本文化方面大体是量的增加大于整体结构的变化,而我们这边的变化,可真大得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说是瞠目结舌,不仅是量在激增,结构性的改变与不断的转型,更惹人注目。
有吉佐和子和杜宣已经相继过世。他们都值得我忆念。跟他们接触不多,但觉得他们都是始终没有恍惚的人。所谓没有恍惚,指的既是生理上没有痴呆,更是心智上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
人到老年,生理上的病变导致恍惚,以至痴呆,有时候是无法抗拒的命运之诡。生理上的种种退化是可以通过积极预防和锻炼来减缓的,而心理上的疾患更是能够以清醒的自我定位来加以排除的。我对自己说,偶尔忘带钥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倘若经常地忘记自己的位置斤两,浮躁抑郁起来,那可真是自我催命了。
这两年,很偶然地到《百家讲坛》录制了关于《红楼梦》的系列节目,又连续出了四本相关的书,反响强烈,书也畅销,但我自己很清醒,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作家”需要本本书都畅销。我自己看重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和特殊文本的《树与林同在》《私人照相簿》这两年都重印了,数量都不大,引不起争论,吸引不了多少眼球,而且,我从一九八六年后半年起,编制也不在专业作家系列,我现在就是一个爱画风景写生画自娱的退休金领取者。“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每天《晚报》到手,必要翻到有找不同漫画的那一版,无论是有八处还是九处不同,我总能一一找全。我很快乐。在仔细看图的过程里,相同处令我想到人己相通,而不同处激励我保持个性。全与人同不是好的人生。有几处与众不同之处,才不枉在世一场。我也许还会再有忘带门钥匙的失误,但我不会有失却自我的迷茫。
谢幕与终曲
至今回想起母亲,在剧场演出结束后,那样重视演员谢幕的表现,还不禁感动。
她不仅会随着大家一起鼓掌,微笑地仰望着走到台沿谢幕的演员,还总是嘴里喃喃有词,发出些感叹赞扬,仿佛人家会听得见似的。她总属于把掌声坚持到最后,直到幕布合拢再不掀开,才意犹未竟地离场的那批铁杆戏迷之一。不等回到家中,在公共汽车上,她就会抿着嘴笑,跟家里人宣布:“今天谢幕六次啊。真精彩呀。”或者说:“别看今天谢幕才三回。其实也很了不起。”她很少有对演出不满意的时候,当然,那也是因为剧目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父亲只爱看京剧,母亲除了京剧,其他剧种比如评剧、曲剧、河北梆子也都喜欢,而且也很爱看话剧,我小时候跟母亲进剧场观剧的次数最多。
母亲重视演员谢幕,当然首先是对演员有一份浓酽的尊重。她说过嘛,应该像爱惜每一篇字纸那样,珍惜每一回观看到的演出。但那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理性支配下的礼貌。母亲有感悟艺术的天性。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跟她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孙维世导演的,金山主演。那出戏展现的生活和人物不仅离我那样一个中国少年极其遥远,其实与一直并没有走出过国门的母亲也很隔膜。但是幕布一拉开,记得第一幕布景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外省农庄花园一隅,穿西服的绅士和穿拖地长裙的淑女慢条斯理地在台上活动着,从树阴下的长餐桌上银闪闪的大茶炊里接茶喝,说着一些很平淡的话,我开始真有些“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不知不觉左腿抖动起来,母亲感觉到了,用右手轻按我左腿膝盖,轻声在我耳边说:“看他们多不顺心啊!”母亲这一句提示,竟让我一下子捕捉到了此剧的情调,我像母亲一样专注地观看,渐渐从那些似乎平淡的对话里,听出了味道,小小的心于是琢磨起来:景色那么美,穿的、吃的、住的那么好,可是这些人为什么那么不快活?……当然,整出戏演完,我也不能说真看懂了什么。演员谢幕的时候,母亲照例感动地久久鼓掌,我也跟着鼓掌。回家的有轨电车上,我跟母亲说:“这戏好。”母亲问:“好在哪里?”我就说:“万尼亚舅舅跟他侄女儿索尼娅说:你的头发真美。索尼娅说:一个人长得不美的时候,人们就会安慰她,你的头发美……”母亲微笑了,笑得像缓缓开放出一朵花,说:“能记住这么几句台词,也不枉你看了这么一出戏,他们也不枉演了这么一场啊。”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话太老了。其实还可以说些“年轻话”——戏吸引人恰是因为不尽如人生,而人生的诡谲其实远非任何戏剧可比。现在回想起母亲带我看戏的种种情景,忽然憬悟:观戏的最大意义和乐趣,是在人生中镶嵌进一些“美丽的停顿”。
母亲带我看了戏,也熏陶出了我的文明习惯。母亲仙去二十年了。现在我进剧场不多了。但一旦去剧场观剧,我总是提前进场,中途绝不“抽签”。我最见不得那些未到幕落就站起来撤退的看客,我总是以真诚的鼓掌和仰望来对待演员谢幕,离开剧场回家的途中,我会回味那些最打动我的片断。
西方古典歌剧正式开幕前,往往会有好几分钟的序曲。多数西方电影的最后,是一边放映详尽的演职员表字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