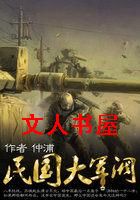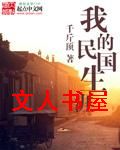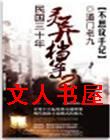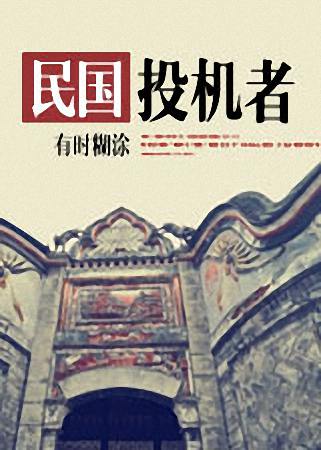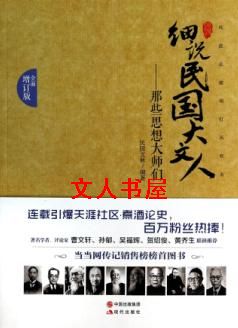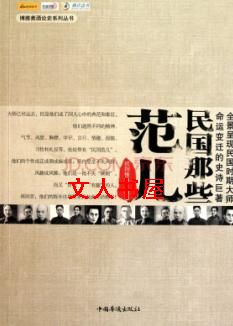民国风景-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定有重要事。9点钟,许广平由海婴和孙儿周令飞陪同,祖孙三代到了董秋斯家。刚入座,还没来得及呷一口茶,许广平便取出一封上呈党中央的信(草稿),内容是关于戚本禹盗窃鲁迅书信手稿一事,并要求追查其下落。许广平把信交给董秋斯看,想听听他的意见。在与凌山的交谈中,许广平不禁悲从中来,一激动,声音突然变得沙哑,心脏病急性发作。她赶忙含服两片硝酸甘油,仍不见好转。海婴见状,匆匆将许广平送往北京医院。当时的医疗系统已被*、“四人帮”一伙人认定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加以重炮摧毁,正常的医疗秩序全被破坏,处于瘫痪状态。尽管许广平是全国人大常委,病历被转到别处,仍未能幸免于临危被拒于医院门外的厄运。等到费尽了口舌,办妥手续,再行抢救,为时已晚。是日下午,周恩来到医院向许广平遗体告别,并慰问其家属。海婴将许广平要求查寻鲁迅书信手稿的遗书交给周恩来。次日凌晨周恩来到许广平家,当面向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读了许广平的遗书。当晚召开“中央*”碰头会,派傅崇碧提审戚本禹,追查鲁迅书信手稿。后来查明:鲁迅书信手稿就被江青藏在她的保密室里。原来江青知道鲁迅书信手稿中有涉及她30年代的丑闻的内容,怕传出去坏事,所以窃为己有私藏。事后,江青假惺惺地说:“是我们没有对她保护好。”保护是假,谋害是真!
鲁迅在赠许广平《芥子园画谱》上题诗曰:“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这是他们坚贞爱情的真实写照。许广平对鲁迅的爱岂止是共同生活的10年,这以后在那阴阳阻隔的32年里,许广平无时无刻不是在以生命之沫“濡”鲁迅,在捍卫这面民族魂的大旗。她是为捍卫鲁迅先生的遗物而倒在对敌斗争的前沿,这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
征引及参考书目:
许广平:《许广平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陈小滢:《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1)
数*人物,岂能只看今朝?
上世纪初叶,是英才辈出的年代,尤值称道的是巾帼不让须眉。仅以五四时期北京女高师而言:苏雪林、冯沅君、黄庐隐、毛彦文、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许广平等,日后的她们或是在各自领域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作家、教授,或是成为反封建、追求女性解放,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英才。让人颇为惊异的是,她们的婚恋、人生遭际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幸。最为悲情的当属庐隐。
初恋男友林鸿俊
庐隐是与冰心齐名的五四女作家。诚如她的名字所昭示:“庐”的真面目已被“隐”去。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她鲜少被人提及,只在近年才“出土”。她的惊世骇俗的婚恋却比她的作品更为世人所关注——性格即命运。
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乃父是举人。命中注定,她生不逢时。庐隐出生时,恰逢外祖母逝日。母亲视其为“不祥的小生物”,情感的屏幕上蒙了层阴影。生母不愿哺喂她,雇一奶妈喂养。小庐隐模样不俊,身上长满疮疥,脾气倔强不讨喜,且好哭。家人均厌恶,差点被父亲葬身江流。喂养她的奶妈看她太可怜,带回乡下自己抚养。庐隐3岁时,父亲鸿运高照,放任长沙知县,庐隐才被接回。3年后,厄运陡至,父亲突然病故。寡母带着庐隐5个兄妹到北京,寄居在舅父的屋檐下。家庭的歧视、冷落严重地伤害了庐隐幼小的心灵。9岁那年,庐隐被送进收费低廉的女子慕贞学院接受启蒙教育,她在“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的情感中度过了灰色的童年。所幸大哥黄勉对她比较关爱,助她考进了女子师范学校,读了5年。庐隐聪明、勤奋,在师范学校时大量阅读古今小说,林纾译的300多种小说,她都看了一遍,被同学称为“小说迷”。她在《红楼梦》、《西厢记》和《玉梨魂》的恩爱情仇中植下了文学的种子。
17岁的庐隐已出落成大姑娘了。但她的长相实在平平,扁平脸,塌鼻子,又矮又瘦。她自嘲“短小精悍”。已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同住的姨母家来了位亲戚叫林鸿俊,曾在日本留学,因父病回国。父不幸病逝,在北京逗留期间,与庐隐相识。林鸿俊长庐隐3岁,他欣赏庐隐的聪明、干练和善良,试托人向黄夫人提亲。黄夫人觉得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拒绝了。林鸿俊很伤感,写信致庐隐,倾诉对她的仰慕,坦述自己幼年丧母、青年丧父的凄凉身世,以及不能与之结为秦晋之好的悲哀和绝望。这信引发了庐隐强烈的共鸣和同情,激起了对母亲的势利的一腔义愤。“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的庐隐,毅然决然地向母亲表示:“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承受。”母亲了解女儿执拗的性子,只好退让,提出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林鸿俊欣然接受,在婚约上签了字。庐隐为林的学费四处张罗,有一位亲戚动了恻隐之心,资助了林鸿俊2000元。
林鸿俊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这时庐隐高中毕业,当时大学不招女生,她便在中、小学代课,游走于北京、安徽、河南之间。两年后,北京女高师招生,庐隐要去报考,母亲极力反对。庐隐为筹学费,又到安徽教了一学期书,积攒了200元,于1919年秋报考女高师,因错过考期在国文专修科旁听。一学期后因成绩优异与同为旁听生的苏雪林转为正式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2)
那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庐隐借李清照的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述志。今天*,明天*,后天讲演,活跃非常。她被班级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福建同乡会代表,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3人年龄相仿(班上年长的有抱孙者),志趣相投。4个人自制统一服饰,上着灰色线套衫,下穿花边黑绸裙,颇有游侠味。4人出入相随,形影不离。庐隐说:“我们4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一时,“四公子”的雅号传遍校内外。庐隐的文章写得俏拔,连自视甚高的苏雪林都说她“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伊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端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庐隐此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纵论社会,阔言人生,倾诉女性的苦闷与烦恼,向往女性的自由和解放。她悄悄地将自己与林鸿俊的恋爱过程写成《隐娘小传》,以表达她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金钱的恋爱观。
但现实是多变的、残酷的。林鸿俊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要求庐隐践诺与他结婚。庐隐以自己还没毕业为理由拒绝。在庐、林订婚后的交往中,两人志趣不同,渐生分歧。林虽经过五四的洗礼,但思想守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特别是林毕业后,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时,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不要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同时,还表示他并不满足自己的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云云。庐隐对林鸿俊这种沉溺于享受的庸俗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还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更为恼火。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性格豪放磊落的庐隐,真的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庐隐当初为“仗义”挺而献身,与林订婚,时下又因道之不同而与林分道扬镳。她的初恋,来也匆匆(草率),去也匆匆(干脆)!令人回味。显然,个中不乏他因。
有妇之夫郭梦良
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郭梦良(1897—1925)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在北京*兼职。在大会上,他的睿智、简短的发言引起庐隐极大的兴趣。那时,男女生分校,还处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大家互不相识。开会时还男女分坐,中间用一条大白布隔成“三八线”。这次同乡会上,为弘扬五四精神,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天作之合。他们由此相识、相知、相爱起来。
郭梦良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有宏图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他是新婚一个月后才入北大的。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一边是已订婚的林鸿俊,一边是有妇之夫的郭梦良。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3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她实在割舍不下。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3)
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她由此正式开始她的文学生涯。
庐隐就是庐隐,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郁结在胸。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从内心是爱女儿的。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可到后来,庐隐闹退婚。也罢。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
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是时女儿出世了。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