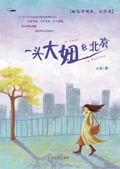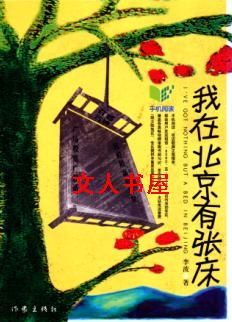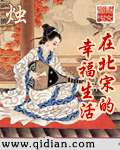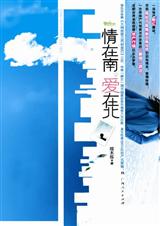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殿、###殿、万福阁。雍和宫既为联络蒙藏,在建筑上也融合了汉满蒙藏各族特色。像###殿顶仿西藏风格的五座镏金宝塔,高达三层的万福阁则属辽金风格,万福阁两侧通往延绥阁、永康阁的飞虹天桥,据说过去仅见于敦煌壁画中,但雍和宫却恢复了这种唐代建筑遗风。
雍和宫不仅是宗教圣地,还是艺术宝库。所藏唐卡、佛像、法器、经卷、壁画等精品无数,但最为珍贵的则有三绝。分别是###殿宗喀巴铜像后的五百罗汉山,由紫檀木雕成群峦叠嶂,五百罗汉则由金银铜铁锡制成;昭佛楼金丝楠木佛龛,上有九十九条盘龙;最后则是万福阁的弥勒佛像,由产自尼泊尔的独根千年白檀香木雕成,在地面上的高度已达十八米,地下还埋有八米,1990年被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
既然到了雍和宫,当然要看看名闻遐迩的密宗欢喜佛。据说雍和宫刚开放时,为了避免民众产生不当联想,曾用红布遮住交合的欢喜佛,也传说欢喜佛是清朝皇帝性教育的工具。我特地前往密宗殿和东配殿寻访欢喜佛的踪迹,但见密宗殿的五大金刚腰缠白布,东配殿的大威德金刚、永保护法、吉祥天母、地狱主、财宝天王也都穿着衣服,因此看不出门道。对于我这样兴致勃勃的寻找欢喜佛,殿里的喇嘛师父不以为然地说:“佛教里哪来的欢喜佛?只有金刚和明王。”
其实欢喜佛说的不是淫乐。据说,金刚独像是镇压的象征,意味着以大愤怒和异教徒(一说是自身魔障)搏斗,最终获得胜利而内心欢喜。拥抱的双身佛像,有人认为是一种了悟的善权方便法门,传说释迦牟尼曾派观音化成美女而和残忍的国王“毗那夜迦”交合,以此将他引入佛门。另有人认为这是密宗智慧与禅定合一的上乘修身法“定慧双修”。
提到雍和宫,不能不提的还有俗称打鬼的“跳布札”。从清朝开始,雍和宫打鬼就是北京百姓迎接新春的热闹庆典。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雍和宫先要举行四天诵经###,从二十八日再举行四天打鬼仪式,以神舞来驱魔除祟祈祷安康。
其实,如果对宗教或艺术没有兴趣,雍和宫仍然值得一游。有时走在各进院落,就能感觉静谧闲适。同样是旅游景点,恭王府花园令人浮躁,雍和宫却将涌动的杂质吸纳,重新吐出一片清和气象。
记得第一次到雍和宫来,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孩在佛像前顶礼膜拜,当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我想,不管宗教曾在人间引起多少纷争,人心对超脱的渴盼,就像在无边黑暗的隧道,追寻遥远尽头的一丝光亮。
。 最好的txt下载网
13何经泰摄影
廖伟棠摄影
春风几度大觉寺
The Weathered Dajue Temple
文冯不二
图何经泰·林崇诚
大约1965年春天,开挖从密云水库到北京的引水渠,机关、学校都参加了义务劳动。那时我正读中学,参加的是北安河到周家巷段的工程。我们住在工地附近一个村子的农民家里,按照学校的要求,每天早晚要学习当年八路军的作风,帮房东老乡挑水喂猪扫院子,因而也时不时的和老乡们聊一会儿。从老乡嘴里探听出附近有一座怡亲王花园,现在还存有戏台等建筑,向西有大觉寺和鹫峰寺,向北有七王爷坟和一座古刹龙泉寺。十几岁的孩子,正是好动的时候,于是白天干活偷懒,晚间就去寻幽探胜,一个星期下来,倒也把附近大致走到了。大觉寺当然也去过,但只到了山门前,并没有进到寺院内,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回到家后,翻看书架上的《帝京景物略》《天府广记》等一些北京历史地理的旧书,才知道大觉寺是京西十分著名的寺院。寺在台山,建于辽代,存有辽碑、辽塔和明代佛像。初名清水院,沿用至金,为金章宗西山八院之一。以后改称灵泉寺,明宣德年间重修,改名大觉寺。寺倚山面东,这是依契丹人“朝日”习俗而建。清初人多欣赏寺内玉兰、银杏、樱桃及泉石之胜,以后则以山麓杏林名擅京师。看了有关记载,觉得十分有趣,很想一探究竟,就邀了三五个同学,下午放学后,整顿装备,骑上自行车直奔台山而去。我们当时的“行头”也值得一提,我的两个同学,一个身背跟女同学借来的135照相机,一个背着军用水壶,我则挎着一枝德国产的老气枪,口袋里揣着几两粮票几毛钱,自觉潇洒无比,威风八面。一路攒行,赶到大觉寺已是星月交辉,依然只得了个“仅及山门而返”的结果。尽管如此,还是兴头十足。归途下坡,车顺势而下,路上也没有什么行人,我们则一路反复高声吟诵着:“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肚子饿了,又找到一家小馆,吃了一毛钱一碗的馄饨,六分钱一个的火烧。那种豪迈,那股子不伦不类的不可一世,恰恰就是当时我们这一伙白袷少年的情怀。
跨入大觉寺的山门时,已是70年代初的某个春天。当时我由上山下乡的地方回北京探亲,到家一看,父亲仍关在“牛棚”,母亲已去了湖北“五七干校”,两个姊姊也分配到外地工作,妹妹在近郊插队。家里房子被挤占,只留一间屋一张床,读中学的弟弟居住,根本没有我的床,于是投奔到一个老同学所在的西山林场,到了,才知道他的宿舍就在大觉寺迤北的老爷山龙泉寺内。
每天早晨,我在林场食堂吃饭,饭后借辆自行车顺山而下,七王坟、鹫峰、大觉寺,几乎每天都去徜徉。站在鹫峰顶上远眺,一川平畴,天气好时可以望见北京城。那时的我不过二十出头,说起来正当大好年华,却已没有了往日的豪情,只觉道路茫茫,不知前途何在。如此惶惶的心境,就算眼前天天掠过大觉寺内的玉兰、银杏、长松、古塔、旧碑,也没有特别注意,印象十分淡漠。只记得山下在修一个工程,进展十分迅速,后来得知,那是为美国尼克松总统来访,对海外直播新闻用的卫星地面站。
再次进入大觉寺是又过了几年之后的70年代中期的春天,那年丛碧词人张伯驹先生说起大觉寺的杏花盛事,准备旧地重游,可我印象中并没有看到过杏花,张先生说,农人不植新树,旧树日老,哪里还会有当年的盛况?当年每逢花期,张先生是必往寺中观赏的,为看杏花,还在大觉寺山门外北侧杏林中建过一个亭子,题曰“北梅”,山门南侧也筑有一亭,名叫“倚云”,是藏园老人傅增湘所建。张先生的亭名取义为杏花花期最早,是为北方的梅花;傅先生的亭名自然是出于“日边红杏倚云栽”诗句。每年杏花时节,两位先生必邀朋友,如夏仁虎、郭则、叶遐庵、陶心如诸老辈在寺前亭上修禊赏花。
如此这般,拣了合适日子,我也追随丛碧老人一行上了西山。行至山门,老人拄着杖率先步入,不想门内闪出一看门人,拦住张先生,说这里是研究所,不得随便参观。张先生大声说,还有没有和尚?看门人当即一愣,呆了半晌,突然躬身行礼说,您是张大爷吧,我就是寺里的长修啊,我已经还俗娶媳妇生儿子了,现在仍在这里干点杂活——此一细节,如此具有戏剧性,所以记得十分清楚。
以后几年,老先生每年都要在春天去大觉寺看花,那时他的白内障已很严重,所谓“看花”,不过雾里相看,嗅嗅味道罢了。但他仍是年年必去,他要人给他讲四周的景物,要听松涛,要听泉声,要和同行的老友——夏承焘、黄君坦、徐邦达、周笃文诸先生吟诗唱和。只可惜每年的诗文,因没有人留意收集保存,都随台的山风飘散了。
14何经泰摄影(1)
白云观里会神仙
Meeting with Gods
in the Temple of White Clouds
文沈帆图杨芳
大概是小时候《聊斋》看多了,心目中的寺观一直是残垣破败,供桌蒙尘,老树昏鸦,日暮时分在人头顶哑哑大叫两声。
而从记事起,白云观的名字就与“春节”、“庙会”等光鲜热闹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对它的刻板印象一直是游乐场所而非宗教场所,大概因为自小到大都要在农历新年中选一天,去庙会的人海中奋力拼突一番罢,与其是为遵风从俗,不如说已成惯性。节目年年总相似:老三样的场面,平日看都懒得看的陈年小吃,了无新意又失却传统的应节耍货,连逛的路线都一成不变,偏偏大人孩子,乐此不疲。
将近六百年了吧,成千上万人点点单纯的快乐,年复一年的,暖烘烘地在这间道观与门前横街构成的丁字形地带上融聚。今年的春节我一如以往地在人流中载沉载浮,一边批评着没有变化的陈旧节目,一边却又慢慢地被那些粗陋花哨的小东小西的浓烈色彩感染,把自己这一点点的简单快乐也加入进去。
省悟到白云观是观而观里应当有道士,缘起于我的一个有趣的小个子同学,某天突然提起自己正为道观浇菜挣零用钱。我听后挢舌不下,恨不能即刻跑去观摩。那时候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尚算超前行为,除了对那位同学与自己同龄却已懂得自食其力的肃然起敬,更多是各种联翩浮想:烈日炎炎下,一个小孩左手木桶右手水瓢,在萝卜缨子上挥汗如雨,看菜园的道士自己却躲在荫凉地里喝着茶,活脱脱一群评书里的惫懒僧道。
但我始终还是没能目击到现场。看现在的白云观平面图里,开放与不开放的部分,都已不复见那位同窗挥洒汗水的菜地;道士们大概也用不着自己亲手种菜吃了。
选个平常时间去白云观是很久以后的事。没有任何法事或典礼的日子里,院落虽不热闹,倒也未见得特别清冷,络绎有三两人来上炷香,或诚心默祷,或走走形式。冬日晴好,苍白的树影投射在青灰色方砖石地上,站在三清阁上,阁楼下那个坐在黑影里的小道士的胡琴吱吱呀呀,虽不成曲,却也如泣如诉,倒给规整的院落添点空寞味道。
这些位道士平时躲在观内清修,做些日常功课,打打太极,练练经乐,根据那本观印小册子上图片所示,个把年长位高的道长偶尔还要抚抚琴、画画梅花。但是一到了农历新年,他们都会放下风雅身段,倾巢出动来抓钱,除了庙会门票、摊位出租、善男信女们比平时加倍的捐献、出售香火蜡烛、符香包等,最叹为观止的是打金钱眼的收入。
进山门不远是窝风桥,桥下无水,悬一巨大木钱在桥拱下,木钱的方孔里有个小小铜钟,逛庙会的人用现金向道士兑换铜元朝钱眼中猛掷,必要打中铜钟而后快,仿佛如此方能与老天爷达成某种商量。屡投不中的人会去继续换钱再接再厉,与角子机异曲同工,只不过对前者的不屈不挠换来的只有当的一声脆响。
据说过去桥洞下还会有修为较高的老道士闭目打坐,一天不吃不动,如今已不得亲见。桥拱下没有高人,只有头脸上蒙着围巾的小道士,怀抱大笤帚,每每趁钱雨稀疏时钻出来回收撒满桥底的铜币,以免桥头的兑换处出现短缺。常为他们捏一把汗,因为那铜币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掷的人又因心情迫切憋足力气,脑袋若挨上一下德行多高都吃不消。不过如此无本万利的生意,一点小小牺牲也值得,看他们卖力撮扫,和大把的朝口袋里搂钱没啥区别。
春节假期间可能是观内大小道众们一年中最紧张的几天。他们要在这几天里应付三百万人,跑前跑后张罗各种事务,庙会结束后还要花很多工夫收拾残局,扫去红绿纸屑、拆除临时摊位、收拾大量垃圾、洗净至少沾了五十万人手上细菌的石猴(该猴刻于山门拱纹上,讹说有疗病功效,游客每年都会排长队摸之,因此浮雕已一年比一年面目模糊)。辛苦归辛苦,“庙会=捞钱大会”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间仅一个糖葫芦摊一天的油水就达两万,可想其中香火之旺,油水之厚,仙凡列众,道友商贩,理当皆大欢喜。
提到神仙,观里供奉的神仙相当齐全,从玉皇大帝到赵公明、孙思邈、八洞神仙、碧霞元君,大大小小至少都能享受到两枚蜡桃,一炷香烟。一直认为中国的神仙满可爱的,因为个个生活气息十足,安胎镇宅、出行入土,上个梁、如个厕冥冥之中都有一路神明保佑,有含含糊糊烧把香就什么都管了的,有分工明确绝不逾矩的,也有什么都不管,专门坐享其成的。因为世俗,所以亲切。
本来道家就是相当贴近群众的一门教派。想想最初修炼道术的人欲望都很明确,炼丹是为了平地飞仙、呼风唤雨、点石成金、长生不老。虽然无意中弄出了火药,被后代子孙以之骄人,动辄拿来说嘴。到如今长生不老的没有一个,黄白之术倒是愈来愈发扬光大。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