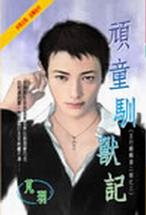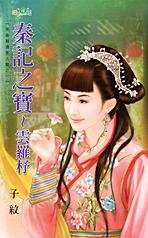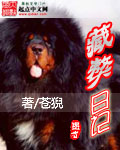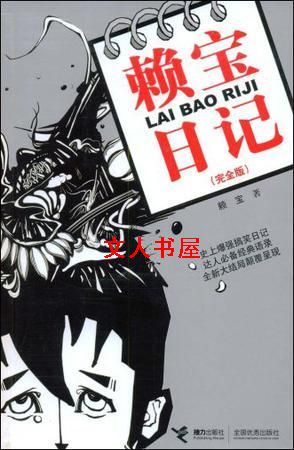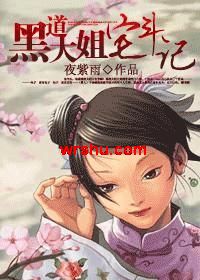新情感笔记-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几个月。
结婚后,“天生就懂得写作”的琼,找了份女侍者的工作,然后回家喂杰克喝豌豆浓汤和咖啡。她最大的收获,是一个不被杰克承认的女儿和《在路上》“卷纸筒”版本诞生的见证人。
靠安非他明驱除睡意的杰克,挥汗如雨地扑在打字机前,以极快的速度不间歇地敲打键盘。谁都不大清楚那些从机器中飞泻而出,带着脆响和汗味儿的文字的价值。琼的眼前是一大卷绵延不绝的打字纸——害怕打字机换纸时阻碍文思,杰克把12英尺长的纸粘在一起,裁成能装进打字机里的尺寸,自制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卷筒纸;浸透汗渍湿乎乎挂满屋子的T恤衫;窘迫潦倒、难以预测的生活。
婚姻的结束或许非琼所愿,但能肯定的是,她没有或者没机会等到辉煌来临。
几年后,杰克在纽约百老汇街口的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时报》,那上面有《在路上》的书评。他在附近小酒馆的暗淡灯光下,将那篇评论一读再读,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高兴不起来,最后回公寓睡觉。
“杰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第二天早晨,电话铃声惊醒了他,他已经出名了。”年轻的作家乔伊斯·约翰逊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成名的那一刻,她以同居者的身份陪伴在杰克身边。
在狂热的文学青年和文学巨匠之间,有时候就像买彩票,你不知道是不停地“下注”,坚信能赢得大奖,还是浅尝辄止,果断抽身。输赢一半靠眼光,一半靠运气。
梅塞德斯两者都具备。
在80岁生日的演讲台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朽名著《百年孤独》的作者,面对一位国王、八位现任或卸任总统、1200名观众,以少有的谦虚向妻子梅塞德斯致谢。
几十年来,这个柔弱而坚韧的女子,扛起所有的生活艰难。她像是知道,总有一天,她的坚持会有所回报。
可真的会成功吗?连马尔克斯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想象一下,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写作,能依靠的只有字母表里的26个字母和两根手指,要是我觉得这样写出的东西有100万人阅读,那似乎是在说胡话。”
结果,他的书“像香肠一样被出售”。那些最初并不自信的文字,给了他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桂冠。
梅塞德斯在做些什么,当《百年孤独》从构想变为文字之时?
卖东西,当首饰,请求房主延长交房租的时间,节衣缩食,源源不断为丈夫提供写作用的新闻纸。书稿完成时,他们只有53比索,连寄书给出版社的邮费都付不起,只能寄出半本《百年孤独》。
如果对马尔克斯的家族稍有了解,你就知道嫁给这样一个丈夫需要多大的勇气。
马尔克斯出生在哥伦比亚小镇阿拉卡塔卡的外祖父家里。身为上校的外祖父指挥过著名的“千日战争”,退役回到故乡后,除了没完没了地追忆往事,就是等待那笔有人许诺过却难以兑现的养老金。外祖母酷爱占卜算命,一个妹妹整天啃吃泥巴,还有许许多多彼此名字相同的得了痴呆症的亲戚……
等候宣判的过程去留两难(2)
从13岁认识马尔克斯到最后嫁给他,13年的时间,梅塞德斯或许已将未来想得通透。这个埃及血统的女孩,有着“尼罗河一般的娴静之美”,她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痛苦与狂喜、天堂与地狱交织着的创作之路,并最终赢得尊重。
相比之下,托尔斯泰娅就没那么幸运了。爱情给了她完全不同的结局——失去了爱人,同时还承担迫害丈夫和人类伟人的罪名。
18岁的索尼奇·卡贝尔斯,嫁给年龄几乎大自己一倍的列夫·托尔斯泰之后,变成了天才和伟人之妻托尔斯泰娅。
这个沙皇宫廷御医的女儿,在克里姆林宫受优雅教养长大的妙龄少女,“原来想凭仗孩子、充沛的精力、青春、健康美貌等资本和他平起平坐”,可她逐渐发现,有时候,尤其是她生病的时候,她“对他来说不过是一条瘟狗”。
冷漠伤得托尔斯泰娅体无完肤,却丝毫不影响她对天职的严格奉行——养育13个孩子,照顾生病的家人,管理田产,清算账目,到法院交涉,一遍遍抄写《战争与和平》,为丈夫出版作品,到博物馆保存和他有关的各种文献,同他争夺财产——托尔斯泰要把著作权(甚至田产)无偿捐赠……
她像超人一样,几乎无所不能。
从18岁到66岁,48年的婚姻中,托尔斯泰娅几乎每天都在追问爱情。她热烈地爱着托尔斯泰,和倾慕他的风流女人争风吃醋,被他的才华、思想打动,却在他的极度漠视中绝望。
多次自杀和出走未遂,越到后来越歇斯底里地要掌控自己的婚姻和生活,托尔斯泰娅最终完全失控——82岁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了,10天之后,文学巨匠死了,她成为罪魁祸首。
在一场场耗尽激情和生命的爱情长跑中,有些人放弃了,有些人坚持着,还有些人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变得脆弱、疯狂、不可理喻。
总会有结局。
等待宣判的过程,去留两难。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天才的阴影里爱情支离破碎(1)
27岁雅恩成为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而他对她的全部了解,仅仅来自她的书。没有历史,没有行李,没有专长,没有名字……他带给女作家一个空白的生命,她可以在上面印上她想印的东西。
卡米耶·克洛岱尔疯了。
与罗丹15年的地下恋情耗尽了她的全部精力。这个有着钢铁意志的倔强女子,终于被击垮。她在精神病院一待就是30年。给家人的信中,卡米耶一直幻想着从那个阴冷潮湿的鬼地方出来,回到泥土、大理石、雕塑中间。可她最终没能实现愿望,甚至连墓地都不复存在。
人们已经不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才华横溢、执著不屈的女雕塑家了。就算被人提起,卡米耶也不过是罗丹绯闻中一个模糊不清的女主角,艺术家们的此类情感经历太过繁杂,谁也不会将“传言”过于当真。如果没有爱情的滋润,没有那些在天才生活里进进出出的女子,他们的创作源泉肯定会枯竭,可红颜知己们的最终结局,多半是堆积于一次次艳遇里的一现昙花,稍纵即逝,只为激发艺术家的灵感而绽放。
在天才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一些传记里,卡米耶只是一个语焉不详的大写字母C。她的幸运在于与罗丹不期而遇,师从于他。两个人在创造手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幸也在此,罗丹太伟大,她永远只能站在巨人的阴影之下。并且,巨人的伟大光环,掩盖了他们品性中的诸多缺陷,自私、不负责、变幻无常。罗丹需要的不过是一个情人兼优秀的粗雕工(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创造风格的趋同,使得卡米耶成为最好的人选),而不是一个和他并驾齐驱的女雕塑家。卡米耶一次次放下自己的工作,完成罗丹一系列雕塑的粗雕工作,她心力交瘁,疲惫不堪。那时,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大雕塑家罗丹站在她的面前,将她完完整整地包裹在自己的影子里。
相比之下,倒是没有艺术才华的露丝更幸运些。她为他牺牲了一切,罗丹感念困境时她的付出。他或许早已不爱她,却给了她无人能撼动的“伴侣”地位。起码,在雕塑家的传记中,有她一席之地,而不是一个字母或者代号。
一些人的名字注定与天才相联。不过,爱情的存在本身已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再一次见证别人的辉煌成就罢了。
为雅恩·安德烈亚打开黑岩楼的大门时,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已经66岁了。她在电话里跟他说:“来吧,不过要带瓶酒来。”雅恩于是站到了她的面前。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胆怯而显得愚笨。她知道他为她远道而来,她对他说:“我认识您已经很久了。”
27岁雅恩成为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而他对她的全部了解,仅仅来自她的书。没有历史,没有行李,没有专长,没有名字。他带给女作家一个空白的生命,她可以在上面印上她想印的东西。
此后的16年,雅恩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杜拉斯身边——除非为了求生而出逃——就像囚禁得发疯的囚徒,有时候必须逃出牢房散散步。他完全没有自己,只有一项艰难的工作:爱她。
不仅仅是情人,还是司机、保姆、秘书、护士、读者。一场长达16年的双人舞台剧,没有观众,只有演员。
幕间没有休息。只有一次,杜拉斯因酒精中毒而深度昏迷。这期间,雅恩写了他的第一本书:《我的情人杜拉斯》。这是一本日记式的编年史,在等待她苏醒的日子里,回忆是他的救命稻草。又过了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杜拉斯像往常一样推醒雅恩,对他说:“杜拉斯完了。”
幕布终于落下。雅恩跟随杜拉斯一并消失。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他的任何消息。雅恩将自己禁闭在令人作呕的小屋里,不洗澡,不起床,不说话,等着像垃圾一样烂掉。
杜拉斯已经离去,可雅恩无法将她从自己的生活里驱逐走。
杜拉斯说:“我要死了,跟我来吧,没有我您怎么办?”杜拉斯说:“写作吧,没必要自杀。别做蠢事。”——她没有留给他任何东西,只给了他自己无所不在的影子。他谈论她,重复她说过的话,按她的要求写作。他的文字里全是她,“像捡木柴一样收集诗句和回忆,以便当孤独像漫长的冬天一样袭来时,能用它们取暖。”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天才的阴影里爱情支离破碎(2)
没有杜拉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叫做雅恩·安德烈亚的年轻人。他给自己的第二本书取名为《我,奴隶与情人》。作为天才杜拉斯的陪伴,雅恩这个名字将不断被人提及,因为爱情或者因为被奴役。
天才的阴影实在太沉重,爱情经不起它的重压。你或许会说,有些人并没有被淹没在天才的阴影里。你说得不错,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那个被萨特亲昵地称为“海狸”的女人,独立而显眼地与巨人比肩而立。可别忘了,此时他们之间已不再有爱情,只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爱情无法因背叛、嫉妒、自私、无休无止的索要而长久,伙伴却由于不可替代、彼此需要而同路。
在名声地位的呵护下,身材异常矮小、近乎独眼的萨特,有着与其外表极不相称的吸引力。或许,波伏娃试图打败她的情敌?谁又知道呢?尘埃落定了,如今,她和萨特一起躺在巴黎蒙帕那斯公墓的同一个墓穴里。
爱情早已死去。
光环笼罩下的卑微肉身(1)
我在这里总结的不过是他的情史,与文学无关。骗财骗色?我可没这么说。
年近30的某一天,巴尔扎克突然宣布,自己不是奥瑙利·巴尔扎克,而是奥瑙利·德·巴尔扎克。可别小看姓氏中这个小小的改动,它意味着这个姓的所有人拥有贵族的权利和资格,身世显赫。
作家有时会将想象与现实混淆,这一点,完全出自老父亲的遗传。出身贫贱农夫之家,喜欢吹牛的老巴尔扎克声称自己担任过皇室秘书,是上流社会诚实正派的一员。不过,老父确实有些本事,他改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在法国风云动荡的年代,一会儿支持国王、皇帝;一会儿支持共和国,不仅未遭池鱼之殃,反倒左右逢源,轻轻松松地攫取了大笔财富。
名利给了老巴尔扎克“讨好”女人的底气和本钱,他春风得意地在50多岁的“高龄”上娶到了小自己32岁的新娘,还在60岁之后添了一堆私生子。在父亲的遗传基因——想象力、对财富的追逐、寻花问柳等等尚未显现之前,巴尔扎克挨过了苦命的童年。
爱财、苛刻、神经质的母亲特别不喜欢这个长子。明明家中宽敞富裕,却愣是在儿子尚不满月之时,就将他送出家门寄养。即使多年后儿子归家,她也让他痛苦不堪,不得不主动逃离。这就能理解巴尔扎克成年后为什么偏爱大龄情人了——他声称“对年轻女孩子深恶痛绝”,她们要求太多给予太少,“40岁的女人愿意为你做一切,20岁的女人则什么也不做。”
不排除这种说法有讨好初恋情人之嫌。母亲以为儿子爱上了名门望族的小姐,没成想22岁的巴尔扎克着迷的却是45岁的祖母级人物德·柏尔尼夫人。她具有他所倾慕的两大品性:贵族姓氏和财富,也让他无处宣泄的青春激情得以流淌。此后多年,柏尔尼夫人身兼情人、资助者、朋友和心理咨询师的多重角色,在巴尔扎克生意场或者情场失意之时,给他庇护和安慰。如此情分,却没能换来弥留之际见他最后一面。夫人病危之时,奥瑙利正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