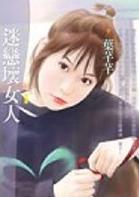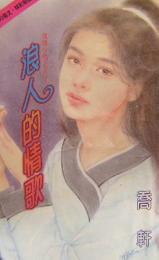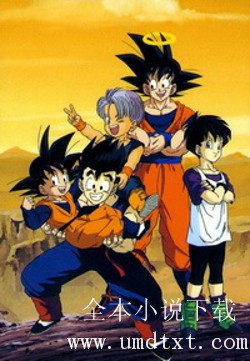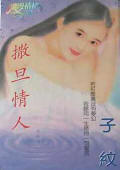读史做女人-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幸与不幸
在大部分时代里,女人是不幸的,而在这个时代,女人却比男人们幸运得多。
作为男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虽在精神上追求自由而自然的“归隐式”的人生境界,但内心深处亦不乏儒家的功业之志。如阮籍“尝登广武山;观楚汉战场;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晋书?阮籍传》)“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 《晋书?阮籍传》) 而嵇康;史载“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 ( 《晋书?阮籍传》) 身为曹魏的姻亲; 不满司马氏残酷的统治; 提出著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 《释私论》) 、“非汤武而薄周孔” ( 《与山巨源绝交书》) 的口号,公开反对司马氏提倡的虚伪名教;面对当时的政局;他只能“超然独迈;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
在无尽的尴尬里,他们永远要在在济世之志与淡泊名利之间走来走去,在匡扶社稷与退隐山林之间犹豫不决,在功名利禄与超逸放旷之间逡巡穿梭—— “居朝端而慕江湖”、“处江湖而不能忘情于魏阙”——永远。
但谢道蕴不需要,她是个女人。
既然消除了儒家“兼并天下”的进取,也就消融了那份进取与退守之间的焦虑与人格冲突,矛盾的两方如果只剩下“放达”一边,她便比身边的男人们多了份生命里的轻逸——
小时候,大雪,叔父谢安于温酒赏雪之余,雅兴大发,问在座的谢氏后辈,飘飘大雪何所似?堂哥谢明接口:“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风起。”——很多人把这个作为道蕴机敏有才敏的例子,笔者却把它看成“轻逸”的另外一个证明。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撤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世说新语? 贤媛》)
谢朗的意象里,雪是“盐”,是人间的,是世俗的,也许从一开始,谢朗就知道自己的人生是继承前辈未竟的事业——你无论怎样飘逸,作为一个男人,肩头上有江山社稷还有家族荣誉,性命前程,所以他只会也只能是“盐”的境界。而道蕴不用,她肯定嫁的不错,只要遵守妇道,社会和上天以及家族都不会找她的麻烦,所以,她活得象“柳絮”那样轻逸悠闲。
幼年读书,谢安问她:“毛诗哪一句最佳?”道韫答道:“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吉甫作诵”指的是尹吉甫写的“丞民之诗”,该诗赞美周宣王的卿士仲山甫,辞清句丽,传诵不衰。谢安称赞谢道韫颇有“雅人深致”。(《晋书?九十六卷》)——
也许从小,我们就可以看到谢道蕴身上迥然于兄弟们的“轻逸”与“雅致”,因为是一个女孩,也正因为是一个女孩,她能轻松地越过男孩子们在功名与退隐之间的难关与挣扎,来到他们所向往但却永远无法企及的“超凡脱俗之境”。
十七。谢道蕴:天上飞鸟的痕迹(3)
3。之轻与之重
四川汶川地震,天灾面前,有几万条生命在这个地球上消失;03年非典的时候时候正封校三个月,经历过一日几百例的极端恐慌之后才明白,在强大的、不可操纵的灾祸面前,个体的生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就这么不堪一击地沉重,生命很脆弱。
于是,日常里恩怨情仇、功名得失瞬息之间无影无踪,我们总以为可以天荒地老,其实,一切都会戛然而止。
由此,也许更能理解谢道蕴那个时代,虽然她消融了男人们那些冲突与痛苦,但是她的轻逸是那样的不堪承受之轻。人,学习了会知道,但是只有经历了,才会懂得,没有办法,有些事情,需要亲身,才会真正的明白。
那个时候她虽然是灵慧的,却是浮躁的。
身边皆天下钟灵秀气,嫁得郎君却是泛泛而已,自是心高气傲的人,回家自是不悦:“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才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 贤媛》)
他配不上她,她惊天绝世,飘若游龙,而他只是禀性忠厚的上才而已,她瞧不起是应该的,但是她并不痛苦,因为从本心里,婚姻在她眼里也算不得什么,或者说,丈夫、甚至男人在她眼里,都算不得什么——
她这样讥笑不上进的弟弟:“你不学进,是世俗之心太重?还是天分有限?”
(“又尝讥玄学植不进,曰:“为尘务经心,为天分有限邪?” 《晋书?九十六卷》)
小叔王献之与友人清谈论文,处在下风,恰巧被经过的她听到了,就叫婢女告诉王献之,愿出来为小叔子解围,于是坐于青绫步鄣之后,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客人都甘拜下风。
(“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晋书?九十六卷》)
那个时候的她,无论是敦厚而渐痴迷于道教的丈夫,还是出色优秀的兄弟们,她俯视而看,自小便被长辈们夸耀出脱,加之天性聪明灵慧,早已进入脱俗容纳之境界——同郡张玄的妹妹很有才质,嫁给了顾氏,张玄每每夸奖,说可以同谢道韫比肩。有一个叫济尼的,常在二家行走,有人问,两个才女谁更优秀?济尼答道:“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玄每称之,以敌道韫。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晋书?九十六卷》)
因为未曾经历事端,在生命的飘逸上,她回头看着那些皱着眉头的男人,一直,是冷笑的——
可是多年以后的一场浩劫,让她突然沉于生命之下。
4。非乱与乱
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让笔者对明代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本以为最黑暗最荒诞的朝代,皇帝荒唐、宦官作乱,朝臣疯癫——其实未必,我们可以奇妙地发现,所谓“资产阶级萌芽”,所谓几大名著,所谓科技发明,都出现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时代:最荒唐与最极端的,但是又是最繁荣和最多元的,虽然出现过几个不理朝政的皇帝,但是往往“君昏于上,而政清于下”——原因就在于他的内阁大臣都非常杰出。
十七。谢道蕴:天上飞鸟的痕迹(4)
与皇权集中奴才主子的清代相比,明朝的皇帝要苦的多,经常要跟朝臣们做拉锯运动,而很多情况下,往往朝臣的意见是对的,原因很简单,朝臣是有选择的,几万人几百万人里挑出来的人尖子,而皇帝,是世袭,是没有选择的——这要感谢隋唐的科举制度。
正是由于隋唐的科举,很多寒门子弟才有机会登上龙门,而在这以前,门第是杀伐人才的最重要的工具,也就因此,有了很多不平,有了很多动荡,东晋算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那个时候,朝政相对固定地把持在王、谢、庾、桓几个特定家族里,执政者也基本出于这几个大的家族——选择余地太小,优秀率自然会降低,而次等士族里的优秀人才由于无法升到高位,自然会心生不满。
孙恩便是。
此人出身次等士族,叔父孙泰为五斗米道教主,当时天灾人祸,战乱频繁,人们不禁要求仙问佛得一个平安,因此势力越发增大,最后孙泰决定教主不做了,换个皇帝当当,结果被司马道父子诱杀,侄子孙恩逃了出来,聚集几百人再次作乱。
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个乱臣贼子型的人物,作乱之时,居然“旬日之中,有众数十万,郡县兵卒,望风披靡”(《晋书 ? 一百卷》)——这是有原因的。统治者的高压早已让下层老百姓不堪重荷,在痛苦挣扎之际,人们自然希望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救赎,而此时,中国最土生土长也是最适合中国的国情的——五斗米教(道教前身)出现了,教主许以来世的种种好处,对不识字的民众来说,确实具有巨大的煽动力量,而对于寒第出身的有志之士来说,四大家族的把持,也让次等士族有志之士无法上身贵介,他们对门阀家族的仇恨可谓由来已久,也就因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孙恩会杀害作为五斗米教教徒的王凝之。
这位老兄果然老实敦厚,最后“天人合一”的不是走向自我超脱,而是直通外太空了。当孙恩大军逼近时,他居然不加设防,相信道祖必能庇佑一郡生灵,每天闭门默祷,第二天对诸将佐说:“我已请得道祖允诺,派遣天兵天将相助,城池可保无虞,贼兵一定会自取灭亡。”——某种程度上,他比城外那个自称教主的人更加虔诚而敬业。
可惜,历史就是历史。
贼兵长驱直入,王凝之及诸子皆遇害,谢道蕴瞬息之间,失去了丈夫儿子和几乎所有的亲人,照理来说,她在劫难逃。她是门阀家族里有名的人物,又是王凝之太守的夫人——孙恩对“统治阶级”的手段向来极为残忍,曾经有次把一个县令煮了,分给县令的亲人吃,谁不吃就把谁肢解了。
他本来作为“起义军”就被史官们瞧不起,加上烧杀掠夺,残害百姓。(“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晋书 ? 一百卷》)。正史里把能用的坏词都用在他身上了“孙卢奸慝,约峻残贼。穷凶极暴,为鬼为蜮。纵窃岷峨,旋至颠踣。” 《晋书 ? 一百卷》)
可是谢道蕴带领侍婢们杀了贼兵数十个,还从这个魔王手里活了下来。
这是一个奇迹。
奇迹起源于孙恩本人。
5。昏与不昏
以前被朋友拉着参加过一次化妆品的传销培训,当那个总监用充满梦幻的语气描述着未来的美好“钱程”的时候,当我们被拉着走在前台按照他们的话语模式发誓颂歌时,我突然发觉有些东西不对——这是一种特有的理性直觉——自己正在被洗脑。
十七。谢道蕴:天上飞鸟的痕迹(5)
象世界上众多人肉炸弹一样,洗脑,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信仰,会让一个人丧失理性的判断,也会让人爆发可怕的潜力,甚至让人忽视生命的分量——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都是以宗教的名义,而以宗教名义的起义,往往声势浩大。
我们常常这样推测一次改朝换代的*,因为“统治阶级的压迫”,因为“老百姓没饭吃了,没衣服穿了”,所以“他们被迫拿起武器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这种推测,只是把老百姓当动物,而没有把他们当成真正的“人”——人都是有精神和心理的。
只要是人,就需要归属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哪怕是那个时代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也需要精神上的慰籍和温暖——这或许可以解释孙恩声势浩大的缘由,这么不堪的一个人,能聚集那么多的民众,是因为信仰的力量。
五斗米教象所有的宗教一样,给了人一种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他设置祭酒这种职位,对信徒生老病死、心理精神都无微不至的关切;树立一些可怕的入教仪式,比如男女合气——陌生的男女经历了这么一遭,想不信也难了;并且许诺了种种美好的陷阱,比如为教主而战可以登仙一类,那么死亡就不再可怕……
也就所以,孙恩觉得走投无路投水的时候,有几百信徒居然自愿跟着他“登仙”,他在民众里面,其实是神一样的人物。
这个人很有意思,虽然不论正史裨史,对他都一律斥责痛骂,但是从史书里的蛛丝马迹里,我一直感觉到了他内心当中所存在的“理性的挣扎。”
他出身于永嘉南渡世族,饱读诗书,虽然世代信奉五斗米教,叔父更是所谓“得道仙人”,但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他遗传了叔父的技术,也没有记载他很得教术真传,只是因为叔父突然被权臣司马道父子诱杀,基于报仇和义愤,他揭竿而起。所以他的起兵,纯粹是偶然。
起义以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把人性的最恶处发挥到极致,从来不像有野心的政治家那样收买人心;听到八郡响应,就欢喜告诉属下:“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想当皇帝了);听到*他的刘牢之临江了,就说“我划江而治,做勾践也行”;听到刘牢之已经渡江,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