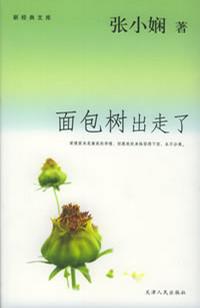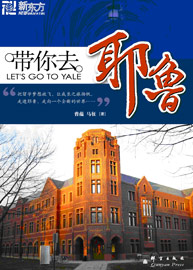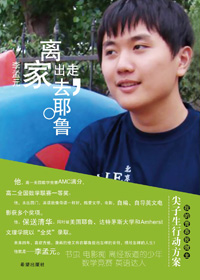离家出走去耶鲁-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在我来到实验小学的第一个学期末,黑板上代表“李孟元”的方格里开始零星地出现几抹红色。白叉从每天两三个逐渐降到每周一两个,最终销声匿迹。白点被引用的频率也明显在减少。而到了放假前那一周,我五天下来的得分竟然是正的。慢慢地,我对赵老师的排斥感日渐消退,随之而来的感动也在慢慢滋长。
从这里开始,我的小学生活走上了正轨。
突飞猛进(1)
就像教练培养足球队员时不仅要考虑战术思路,还要为球队本身的打法风格定下基调一样,母亲在不同阶段也会根据我成长情况的变化来制定不同的方针。在她看来,我在当时应该已经拥有不输给任何同龄人的能力和潜质,只是迫于陌生环境外加缺乏自信而难以彻底展现。因此,她把最新的教育原则定为“鼓励”。
“鼓励”说来容易,但若掌握不好分寸就很容易沦为“安慰”。虽然小孩子在体会上会较成年人略显迟钝,可是被“安慰”得过于频繁也难免会造成性格上的缺陷。幸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母亲有着(在我看来)举世无双的造诣。
举个例子:我的口才。
我在1岁半左右开始学习汉字,而且因为之前提到过自己有些语言天赋,一直以来也没遇到什么障碍。尽管儿时看的第一本汉字书是什么题目、什么内容现在早已回忆不起来,但是清楚记得一年级开始时,每月一期的《儿童文学》逐渐成为了我的必看图书。待转到实验小学以后,我又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下来。于是每隔几个星期,在《米老鼠》席卷班级之际,我总是很非主流地独自一人捧着一本《儿童文学》贪婪地吮吸着其中的养分,任凭周围同学们欣喜若狂的在“鸭堡”中寻找乐趣、流连忘返。其实在花一整天看完《儿童文学》之后,我也会打开自己的那本《米老鼠》。只可惜等到那时米老鼠和唐老鸭基本已淡出了班级同学的视线,于是又剩下我一个人对着那显眼的彩色卡通人物,旁若无人地捧腹大笑。话说回来,数十本《儿童文学》的历练搭配上课内的学习,这些都为我能较快阅读高水准的文学作品打下了坚实基础。等到*岁的时候,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小说故事。可惜那会儿也许是年纪小,也许是品味不够,反正一年下来并没有收获什么让人终生难忘的佳作。总而言之,从那段岁月起,我便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看完上面一段话,容易产生“这孩子语文还挺不错嘛”的印象。事实上,二年级的我虽然读书成瘾,堪称同龄人中的榜样,但在语文最精髓的表达能力方面却存在着致命缺陷。作文也就罢了,虽然偶尔思路混乱,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还差强人意。我真正的问题是在口头表达上面。
之前提到我小时候讲笑话能把自己讲哭,还真不是夸大其词。试想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读到*笑话一则,珍藏许久后终于鼓起勇气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然而张嘴之后,却发现只描述背景就花了很长时间,接着还没抖出包袱自己就先笑了起来,随后眼睁睁看着周围人的注意力在冗长的陈述中一点点涣散,最后随着别处一声巨响或一阵怪叫,所有听众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争先恐后地逃之夭夭。这种事情发生上百次后,对那位天真少年的纯洁心灵造成了多么沉重而残酷的打击,就真不是一般同龄人所能够体会得到了。
在这最危险的时刻,母亲站了出来。一次又一次,当我在流失一个个的听众,开始惴惴不安地东张西望时,母亲总会如期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面带微笑,全神贯注地看着我。她脸上的表情不是怜悯或无奈,而是令人信服的好奇。一看到这些,我又会重新燃起说话的勇气,从而把剩余的部分一气呵成,也将自卑和失落一概抛诸脑后。母亲从来没有教过我话该如何说,更没有泼过一次哪怕是略低于常温的水。而与此同时,我从未觉得自己只有在母亲的“帮助”下才能把想法顺利付诸口头,因此也从未有过被人“施舍”的伤感。母亲的政策能达到这样的完美效果虽然与我自身的天真和迟钝有关,不过至少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母亲拿捏“鼓励”的分寸有多么恰当。就这样,我慢慢能做到在没有母亲的场合也同样能神色镇定、娓娓道来了。当真正开口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看了那么多《儿童文学》果真不是浪费时间。很多精彩的想法、传神的语句总会在最恰当的地方伸出援手,让我在侃侃而谈之间居然偶尔也能妙语连珠。等到三年级开始的时候,李孟元能说会道的本事已逐渐在班里传开了。每逢课间休息,总能看到十几个人围在我的座位周围,满脸期待地等着我给他们讲故事。从刘宝瑞的相声到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从黑猫警长的剧情到蓝皮鼠大脸猫的主题歌内容,只要是需要上下嘴唇一碰来表达的事物,我几乎能在那十分钟的闲暇里讲述一遍。一些同学听我说书听得如醉如痴,甚至开始有些厌恶听到上课的铃声。而每当我看到他们脸上写满了“意犹未尽”的字样,在铃声中悻悻离去的景象时,我稚嫩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直至此刻,我才相信自己已经走出了“张口结舌”的阴影。
突飞猛进(2)
在实验小学的四年里,我在很多方面有了显著提高,其中最明显的要数这样几条:体重、脸的尺寸和数学。
抛去前两条不说,不妨来看看数学。
提到我的小学数学,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小博士、500 港币、华校。
授予“小博士”活动听着好像有些滑稽,却是另一项极富实验小学特色的活动。每年十二月前后,实验小学都会在各个年级举办一场大型奥数考试,而各年级的前几名都会被授予“小博士”的称号并奖励丰厚奖品。奖品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那顶庄严的博士帽。想象着,博士帽戴在头上,一缕金黄色的流苏从耳边垂下。手中的奖状在颁奖舞台的聚光灯下格外耀眼。再看台下一群面带崇拜眼神的同龄人,一种莫名的成就感便会油然而生。
可惜事与愿违。所谓颁奖,就是把考进前十名的一帮孩子集中到一起,往每个人头上扣一只红纸壳一样的锅盖状物件,再往每个人手里塞一打色彩缤纷的本子,合张影然后拍屁股走人。这种待遇,我在实验小学享受了四次之多。
二年级初来乍到,一头雾水,结果首次参加“考博”不出意外地一败涂地。还好根基在,实力在,一番努力之后,那些“幻方”、“鸡兔同笼”等还没上学就开始钻研的知识立即就派上了用场。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成功跻身前十,拿到了第一顶博士帽。
不过就在同一年里,我斩获了一件与纸糊的博士帽相比,分量不可同日而语的荣誉:一块金牌。
那次竞赛被称为“四国国际学术评估”,光听名字就像香港那边传来的东西,事后证明果然不假。赛事具体背景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依稀记得是一次同时在中国大陆、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英国展开的小学生水平测试。试卷分英语、数学等不同科目,而我报考的是数学。拿到试卷才发现,该考试虽然名头唬人,但难度却不高,与同年级的“小博士”测试相比还要逊上一筹。然而考过试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越简单的考试越难从人群中拔尖。近几年来,这一点在我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从初中开始,我就常常在全班重大的考试中屡屡冒头,却在各种天真无邪的基础测验里落马,实在像极了金庸小说里的“独孤九剑”,当真是敌强我强,敌弱我弱。还好,九岁时的我尚未具有以上的不足,于是在填写“评估”时成功迈过了无数陷阱,看穿了试题中的骗局,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以满分的成绩摘得桂冠,也成为该考试历史上唯一一位数学满分的三年级学生。与“小博士”奖的几个笔记本相比,“评估”委员会真可以算得上慷慨,从香港空运而来的奖品包括一只鹅蛋大小的金牌和五百元港币。金牌固然手感好,固然美丽,但与现金相比就少了那种魅力四射的气质。发来的信封里装着一张500 港币的钞票,这是我短短九年人生当中的头一笔收入啊。我拿在手里一动不动地欣赏着,生怕稍有不慎一切就会突然消失,空留闹钟的巨响在耳边轰鸣。凝视中,只见港币上,一只威风的雄狮面带微笑望向远方,仿佛在对我低语:我是第一个,不是最后一个……那一刻的我,想必眼神中会流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贪婪……
事实上,在这次带来巨大收益的考试中,数学的气氛并不是很浓。相比之下,我倒是长了很多见识。比如第一次用机读卡作答;比如第一次出现答题时间不够的危机等等。刚考完时我还心有余悸地感叹,心想再也不会遇到这种让人答题时间不足的奇怪现象,孰不知仅短短3年之后,它们就再次“粉墨登场”,成为我中学生活的家常便饭。
突飞猛进(3)
到了四年级时,我身边的数学气氛骤然浓郁了起来,其源头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华校。
我初二那年,人大附中举世闻名的华罗庚学校改称“仁华学校”。然而,只要现在的初高中同学提起彼此小时候每个周六赶往的那个共同目的地时,都还是会沿用老称呼:华校。
华罗庚学校有一个门槛很高的统一考试,一场考试下来就能刷掉相当数量的候选人。而即使对考取的学生,校方也并非一视同仁,他们会根据分数档次把各个年级分为1至11 班,成绩越高者进入班级的数字也就越小。不同班级享受不同水平的师资和不同难度的课程。在日后小学升初中的各项指标衡量中,学生在班级的学习履历也会成为重要参考。人大附中无处不在的精英制度,从这个选拔“预备队”的过程中可见一斑。
四年级的我,被分到了11 班。不是因为我考得太差,也不是因为我实力不足。这个尴尬的分班结果其实在意料之中。毕竟,我在四年级压根就没有参加入学考试;毕竟,考试的当天我人正在香港参加一场英语剧大赛。
总之,第一次面对华校的课堂就是坐在“最差”的班里,在很多人看来恐怕要用“开门黑”形容了。好在我的性格和经历都让我对所谓“最差”没有任何抵触,也好在教我们11 班的数学老师,跟“差”这个字简直完全无缘。
我们的数学老师,人很年轻,又瘦又高,鼻梁上一副清秀的眼镜更衬托出一身的书生气质。来教室的第一天,就见他两手空空,只有兜里揣着一本华校的“思维”教材,即数学课本。走上讲台后,他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也在不经意间暴露了自己获得过数学国际奥林匹克金牌的身份。当然那个时候我对IMO(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a )连个理性的认识都还没有,不过一听说是世界性的奥赛金牌,那比这再高就要冲出地球了,看来果然不是等闲之辈,心里对这位老师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敬佩。“眼镜男”也不含糊,上来就用一道让人吐血的试题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敬畏:1234567×1234567=?
当几个带了计算器的同学陆续发现计算结果超出了机器屏幕所能显示的范围之后,全班陷入了一片绝望的安静之中。“眼镜男”扫视了一遍台下束手无策的弟子,撩起袖子背过身,开始在黑板上书写。只见他动笔如飞,眼神飘逸,瞬间便作出了几个等式。15 秒之后,他侧过身,在黑板上一处显眼的地方开始书写了一大串数字。他写完后,回过身,低下头扶了扶眼镜,淡淡地说:“看看对不对?”
当时所有人都被这魔术一般的表演所震撼,整体一副“老师我们崇拜您”的茫然表情,直勾勾盯着老师。也没有人考虑到那句“看看对不对”是多么的不合理,都只顾一个劲寻问速算的诀窍。老师也不避讳,当下便坦白自己在速算方面有着一技之长,于是从速算开始,第一堂课进入了正题。
顺带一提,那个算式的答案是1524155677489 。“眼镜男”用15 秒算出的答案没有任何错误。
就这样,带着对老师的敬仰,我顺利读完了四年级的华校。在“小博士”荣誉的战场上,我凭借从人大附中带回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轻松拿下了第二顶博士帽,并在当时名列年级第三。此时此刻,数学俨然能以“特长”的身份出现在我的简历中了。
突飞猛进(4)
之后一年,就有点一帆风顺的味道了。五年级那个暑假,我考完华校分班测试便和父母一起前往江南游玩。沐浴在吴越水土芬芳而滋润的气息中,不禁有种恍若隔世、似曾相识的依恋之感。仅此一遭,江南水乡的情结便已深埋我心。行将至末,母亲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等她讲完话,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