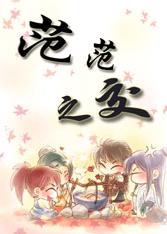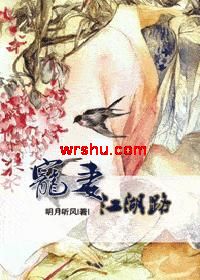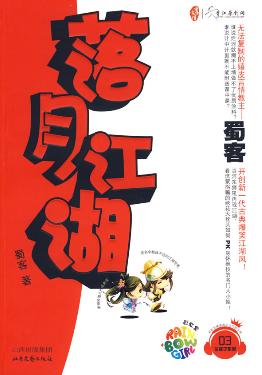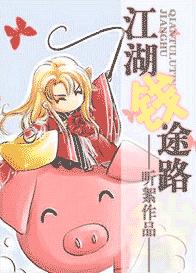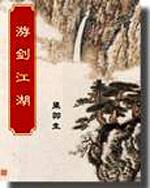江湖丛谈-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身,我只好不去。由于黑这种向别人谈话的口气就可以证明,北平的老柴家是不吃老荣的揉杵的,是不联络老荣的。在外省市商埠码头丢了东西,在三天之内找着小绺头儿,或是有势力向官人追究,谁能把东西找回来。到了北平则不然了。
敝人在从前很纳闷,凭什么很好的人不作正事,不学点手艺,他们老荣们愿意当小绺,虽是手底下做活好的能赚个吃喝嫖赌抽,眼前快乐。若是遭了官司有多么可怕呀!俗语说,“屈死不告状,穷死不作贼”,官司不是好打的。“净见贼吃饭,谁见贼挨打”,干什么不是吃两顿饭哪!有深知他们内幕的人告诉我说,小绺这行儿,有师傅有徒弟。我曾问过:“好好的人谁肯拜师学当小绺呀?”这位深知内幕的某君先叹息了一声,然后才告诉敝人:他们小绺这行人,师收徒不是徒弟找师傅,是师傅找徒弟。凡是小孩到了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时候,当家长的教育子弟最难,小孩的知识最幼稚,大人不栽培,做父母的对不住儿女,若是教育他们,栽培他们,还要得法,不可过严,不可不严,不能不慈,不能过于溺爱,得督促小孩学能耐,还得拢住小孩的心。倘若不得法,小孩子受挤对,他急了只有偷偷地远远一跑。他们老荣若是要收徒弟,就专在热闹场儿的地方寻找这路偷跑的小孩,带到店里住着,足吃足喝,天天带出去足逛。小孩们到了他们手里,如同上了贼船一样,休想下得来!抽鸦片、扎吗啡都能戒除了,唯有当小绺的,洗手不干改了行的,实在是少啊。可是小绺的徒弟,亦不写字,亦没保人,亦没有学多少年的期限,只要学的会偷了,不良的印象越来越深,懂得离开他师傅啦,翅膀儿硬了,就偷着一跑儿,躲开他师傅完事。敝人将这种情形写出来,不是给社会的人士添不良的影响,是叫一般有了儿女作家长的,栽培教育都要得法,不可过于放纵,不可过于严厉,否则孩子跑喽,被他们老荣拢了去呀,那可怎么好!还有,手艺作坊掌柜的,商号的经理,对于学徒的小孩,非得恩威并行才能教出好徒弟,有利于人,亦利于己。如若有威无恩,将徒弟挤对跑,徒弟入了邪途,于个人的道德上亦是有亏呀!这些话是我一份爱护一些知识薄弱的小孩之意,阅者可别错想我是刻薄呀。
挑青子生意之内幕
在从前,有一种逢集赶集,逢庙赶庙卖剃头刀子的生意,江湖人管他那行儿调侃儿叫“挑青子”的。
做这种生意的亦是一种“笨头”搁念(江湖人管做买卖的资本调侃儿叫笨头),他们背个包儿,有个几把刀子,打走马穴儿,顶个“凑子”就能挣钱(江湖人管赶集上市调侃儿叫顶凑子,赶庙会,调侃儿叫顶神凑子)。到了集上,找个过路口儿,将包儿一放,左手拿着一缕儿“苗西子”(江湖人管头发调侃儿叫苗西子),右手拿着一把剃头刀子,就能圆粘子。他说:“我是刀剪铺子耍手艺的,从幼小儿学了这份打刀子的手艺。总给人家耍手艺,挣不了多少钱,我要自己做个买卖,因为本钱小,开不了铺子。耳挖勺里弄芝麻——小鼓捣油儿。自己的手艺在家里打了几十把刀子,来到市上卖。”他嘴里叨叨念念,瞧着人们都围满了。他说:“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试验。咱们这刀子受使不受使,咱们当面试验试验。”说着他把左手的那缕头发一攥,叫人瞧着足有四十多根,用剃头刀的刃儿对着那缕头发,用嘴一吹气,那缕儿头发就全都断了。围着的人们瞧着他那刀刃如同迎风斩草似的,谁不爱呀。剃头的手艺人使用的刀子虽快,到了剃头的时候,还得用热水把头发洗好喽,抹上洋胰子才能剃哪。他这刀能将一缕干头发一吹就断,较比剃头棚儿手艺人用的刀子还好使哪,谁不买呀。他把刀子试验的人人都要买啦,他又自言自语的说道;“这刀子能把头发割断,大概许是净能动软的,不能动硬的,咱们动回硬的叫众位看看。”说着话他一伸手,从包儿内取出一根锈铁棍儿,有核桃粗细,他往那小凳上一坐,把铁棍用腿夹住了,拿着那剃头刀儿往铁棍上愣刮,哧哧的直响,刮的往下掉铁末子,刮完了他举着刀儿说:“众位瞧瞧。”围着的人们一看,那刀的刃并没有受伤。他说:“咱们这刀是材料地道,手艺降人,才能那样。众位要买这样的刀子,到了刀剪铺得卖你三毛钱一把,我这是头趟来赶咱们这集,张天师卖眼药——舍手传名,名不去,利不来,小不去,大不来,这趟我是不赚钱,只卖个本儿,把手工白饶上,卖两毛钱一把。那位说我全要了,都要我可不卖,我就卖十把刀子,过了十把刀之外,我还卖三毛钱一把。”说到这里把脚一跺道:“我今天豁出去赔本了,卖一毛钱一把!有要的伸手。”他说到这里,便有人买,十把刀眨眼卖净了,一块大洋到手了。赶一个集就卖这么三四回,几块大洋到了手,除去本钱能赚一多半儿。
在从前,我看他们当面试验,东西好,价钱便宜,要买他一把哪!有个江湖人对我说过,他们卖的刀子是“里腥啃儿”(江湖人管假东西叫里腥啃儿)。我说:“他那刀子能够吹毛就断,刮铁棍,怎么会是里腥啃哪?”他说:“卖刀的能够吹毛断发,刮铁棍,那是他们练好的‘托门’,要是到了别人手里就不能刮铁棍了,一刮刀就毁坏了,断毛断发,净吹就不断了。他们把‘托门’练好了,先说个大价钱,后来往下落价儿,由两毛一直落到一毛钱,调侃儿叫‘海开减卖’,‘催啃的包口儿’。做这种生意的分为三样儿:一种是顶凑子,使托门儿,海开减价,挑的是里腥啃;一种是用尖局的啃儿,走常穴的。什么叫尖局的啃哪,就是真正的地道的好东西,要是摆个摊子等主道候客,那可卖不动,赶个集走几十里路亦就能卖三两把,不用说赚钱,就是本钱亦卖不出来。若是逢集便到,挑尖局的东西,走常穴、卖出主顾来,细水长流,亦能获利。不过是慢点,利钱又薄,日子又长,那样做法亦是百里挑一呀。还有一种假装剃头的手艺人,预备一块磨刀布,一个刷子,几把刀子,在各集市上摆摊出卖。有些人疑惑他那刀子一定好使,看他那样子一定是剃头的手艺人,要卖了家伙改行似的,就有人买他那刀子。可是他将那刀子故意弄成了旧的才能成哪!在早年社会的风气不开,都不讲求卫生,剃头刮脸都是找个剃头棚儿,那剃头棚儿都是破烂不堪。社会人士不尚奢华,都是克勤克俭,花个几吊钱买把剃头刀子,又刮脸又剃头,亦是很经济的办法。那时候各大都市、各大商埠都有做挑青子的生意的。到了如今,无论穷富都讲究修饰外表,剃头匠改为理发师(教给我念书的老师也改为教员了),剃头棚改为理发馆。社会的人士都日趋浮华,谁还花钱买把剃头刀儿自己剃头刮脸哪!卖刀子的生意可就不在都市省城、商埠码头卖了,都改了路子到乡间去了。如今挑青子的买卖都做“科郎”去了(江湖人管农人、老乡们调侃儿叫科郎)。再过些年,挑青子的生意恐怕就要天然地淘汰了。
磨杵的生意
江湖人管到乡下串村庄镇去做生意,调侃儿叫“磨杵”。磨杵的买卖亦有好几十样,先由那前些年摇铃卖药的说吧。他们都有个皮包,内里装些个瓶子、罐子、装着丸散膏丹,有旧式治外科疮症刀剪家具,有扎针的针包儿,把这些个东西装全了,说行话叫“啃包”。左手提着啃包,右手拿着“虎撑”(管摇的那串铃调侃儿叫虎撑),走进了乡村的胡同里,哗啷哗啷摇起串铃,乡间男妇老幼听见这声儿,就知道治病的先生来了。有病人的家便请他进去。他一入“窑儿”(管进到病人的家内叫入窑儿),得先把簧儿。他们把簧亦是按着那大方脉的医生“入嘿”一样(江湖人管请大夫治病叫搬嘿,管大夫到病人家叫入嘿),使那“望闻问切”的诀窍。譬如,一进屋,六月天气,正是暑期时,见病人穿着棉套裤,不用问他什么病,一望而知是得了寒腿病了;若是病人脸上涂着黄土泥。便知得了偏头痛、牙痛的病啦;若是病人趴在炕上不住地哼哼,手捂着肚子,一望而知是得了肚腹痛的病啦。他们到了病人的屋内用眼把簧,把病人的病猜出个###成啦,落座之后先“粘弦”儿(管给病人诊脉,调侃儿叫粘弦),最叫人佩服的是他们一粘弦,准能把病人所得的病是怎么得的,得的是什么病,全都说的分毫不差,叫病人信服他的脉气好。据江湖人说,给病人评脉的时候,能诊出得的什么病来,要说对了,那种方法一步叫“粘啃条子”,有了病叫“有粘啃”。他们拿着串铃卖药的,拜师入门,头行儿就学粘啃条子,男子有十几样条子,女人有十几样条子,老年人有十几样条子,小孩有十几样条子。那条子分为:咳嗽条子、痨病条子、筋骨麻木的条子、血分不调的条子,合计起来总有百十多个吧。他要是诊脉的时候把病人的病原说对了,先不给治病,先要“水火簧”儿。譬如他问:“你这病请医生治过没有?”病人说:“咳,先生,我都治腻了。”他听后就知道这家是有钱的,要没钱哪能成天价请大夫吃药呢?请个大夫,出诊费,连抓药没个两三元不成,他要是治腻了,几十元钱就花出去了。别看他治腻了,还能挣他的大钱。社会里有两句牢不可破的话,是:“穷不离卦摊,富不离药锅。”人有钱身体就娇贵,人要穷了,不用说花钱请大夫抓药治病,连吃饭的钱还没有哪,有了病,就算是认了命啦,该活死不了,该死活不了。譬如,问那病人:“你这病治过没有?”病人说:“我疼了半个月啦,还没治过一回哪。”那卖药的先生听着就凉啦。这人但凡有钱绝不能半个多月不治病,这个买卖撑死了亦就挣上两毛洋。
凡是做这种生意的,一给病人沾弥,就得先要水火簧儿。若是真穷,亦就不用多挣了。若是有钱的人家,不多挣钱又挣谁的哪?那病人虽说他治腻了,卖药的先生更会说:“弹打无命鸟,病治有缘人。该着一百天的灾难,九十九天亦好不了,若是该着你消灾,该着我露脸,一治就好。”病人听他说的这几句话,觉得很为有理,就叫他治治吧。他们磨杵的先生亦有几道“样色”。譬如病人得的是肚腹疼痛,他就先使“插末”,他们管扎针调侃儿叫做“使插末”,用针往病人身上一扎,从包内取出一个罐子来,他把针拔下来,用火纸点着往罐内一扔,把罐子往针眼上一扣。他向病人说:“扎针是按着穴道,有:四阴针、四阳针、四大总针、八法神针、九转还阳针、马丹阳十二针、鬼门十三针。何谓四大总针哪,《针灸大成》的书上说的是:肚腹童流、腰背委中求、头顶刺列缺、面口合谷收。针针针,不差半毫分,能用十副药都不动一分针。扎一针胜似吃十副药。扎针拔罐子,病好一半子。”他说这些话,病人亦是爱听,少时间他用手把罐子起下来,猛一翻个儿,叫罐子口朝上,他叫病人瞧那罐子,病人往罐里一看,只见罐内又黑又紫,粘粘糊糊的,有半罐子脓似的。他向病人说:“这一针扎在了病上,把你这病拔出一多半来,今天晚上再吃副药,回头我再给你贴帖膏药,明天就好啦,复旧如初。”不用说病人听着高兴,阉家老幼听着都是痛快的。于是他叫把罐内东西,倒在院内埋了。本家是当面瞧他把病治出来,焉能不佩服他呀。他由包内取出一帖膏药,贴在针眼上,又取出一包面子药说:“你们今天晚上叫病人吃下去,夜里拉出几泡屎来就好啦。”病人说:“先生,我要好喽,忘不了先生的好处。给先生多少钱哪?”这先生说:“若是按规矩,扎针就得一块钱,这帖膏药一元二,面子药是八毛钱,一共三元钱。得啦!针白扎了,药钱我取个本吧。你们给一块五毛钱就行啦。”本家的人见针是扎了,膏药亦贴上了,好好地给人家块半大洋吧。先生治下“柳丁中的拘迷把”(柳丁中拘迷把即是块半钱),收拾包儿走了。到了晚上把药叫病人吃下,本家的人都要瞧拉出来的是什么,谁想肚子咕轳咕轳直响,整整的响了一宵,一泡屎亦没拉,直到第二天早上肚子里还是直响。阖家老幼都纳闷儿,不知是怎么回事,你一言,他一语,其说不一。到了吃完早饭的时候,就听见门外哗啷啷串铃响,卖药的先生又来了。本家赶紧就请这位先生,向他问问吧,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卖药先生头天挣了一元五毛,那是头道杵,第二天他又挣二道杵来了。他还是有把柄,能料着本家准得请他的。二道杵如同在手里攥着一样。他用罐子从针眼拔出来的那东西,是和戏法一样,原来在那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