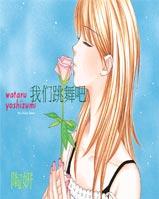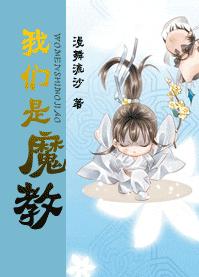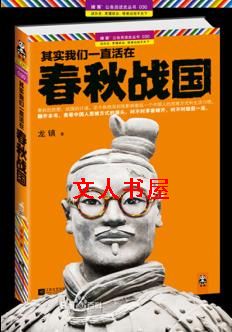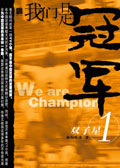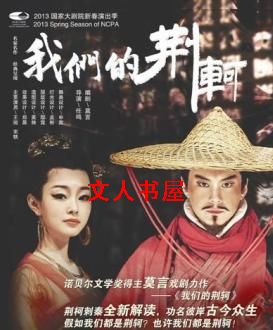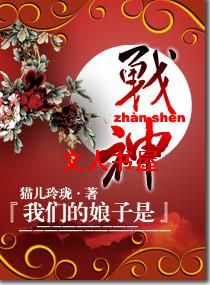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98亿元,是1997年底的33倍,首次超过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消费贷款余额的86%,基本实现了房地产信贷结构的调整。住房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居民购房的支付能力,已经成为居民提前实现住房消费的重要手段。
无数时间点上的瞬间闪耀,都是中国房地产业史上的清晰坐标。1990年,我们无法回避一些人,有的让我们扼腕,有的让我们惊喜。
孙宏斌无疑是极具传奇色彩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90年,对孙宏斌来言,是巨大转折的一年,是从联想“少帅”成为“阶下囚”的一年,是充满乐观理想主义情绪的青年孙宏斌遭遇巨大现实残酷冲击的一年。
1990年3月,柳传志在西山宾馆召开联想高层会议,主要目的是把孙宏斌从企业发展部主管的位置上调开。
柳传志认为孙宏斌的问题确实严重,独立倾向明显。他认为:“孙宏斌努力想形成企业体外的循环,不在监控之下进行他们的运作,已经有财务失控的问题。他们说这种运作的成果还是会归到企业旗下,但是我们是不允许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会归到企业,这不好讲,外地分公司的人都由他来选拔由他来负责,这种做法很危险。”孙宏斌还办了一份《联想企业报》,宣称:“企业内部利益高于一切”。孙宏斌的小动作不言自明。在柳传志眼里,他已有拉帮结派的嫌疑。
柳传志此后找到孙宏斌,让他把几个吵得凶的下属开除。孙宏斌不同意。类似的谈话进行过几次,孙宏斌的态度都很坚决: 不同意。最后一次,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这几个‘青瓜蛋子’?”
“我要‘青瓜蛋子’”,孙宏斌说。“柳总,开除他们的理由不充分,这么做,我在这个部门还有什么威信?不是他们不能开除,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开除。只是给你提了点儿意见嘛。”
意气用事的孙宏斌完全堵死了退路。
更为重要的是,孙宏斌和手下随后在北京大学芍园聚餐,饭局上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在联想2004年作出的《联想就孙宏斌事件的说明》里,提到“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孙宏斌说,当时,“卷款逃走”之类的话他手下很多人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在芍园餐厅也说了,但他自己没有说过。
这次愤怒的聚会被传了出去。也有说法是,孙宏斌的人中,早就有了柳传志的“无间道”,“无间道”迅速把聚会的内容通报了柳传志。
在创业早年间,一个商人蒙了柳传志五万块,急得柳传志天天去堵此人,恨不得直接拿板砖拍他的脑袋。这会儿可不是五万,孙宏斌控制的金额远超于此,柳传志没法不着急。
柳传志决定再跟孙宏斌谈最后一次,还是谈崩了。第二天,柳传志亲自主持召开企业发展部会议,宣布自己暂任经理,孙宏斌另作安排。会后孙宏斌就被送进了看守所。一个月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
两年后,1992年8月22日,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五年。
孙宏斌入狱的时候,孩子刚刚出世。
1994年3月,即将出狱的孙宏斌与狱警到北京采购物品,托人请柳传志在一家川菜馆吃饭。席间,孙宏斌向柳传志道歉。他的诚恳感动了柳传志,柳当场表态:“我从来不说谁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你是我的朋友。”
也正是孙宏斌的这次道歉为他自己赢得了一次机会,出狱后试图重整旗鼓时,孙宏斌得到了柳传志的慷慨相助。这才有了后来搅动房地产市场一池春水,而被王石称为“害群之马”的“顺驰”。
后来有人这般理解孙宏斌的这段经历: 如果他没有1990年的一些恩怨,也许就不会有“顺驰神话”,更没有神话的破灭。
当今业界所认可的最富有、最低调、最神秘的朱孟依,是较早接触房地产的有心人。80年代中期,广东丰顺县城镇商业刚刚兴起,朱孟依所在的镇不少人都在路边摆摊做生意,他想: 何不将摊点集中在一个地方,既热闹又方便,还好管理。于是他去找镇政府,提出由他出资建设商业街,只要求按比例提成业主租金。镇领导喜出望外,立刻答应。就这样,20岁出头的朱孟依凭借过人的眼光,挖到了第一桶金。
1990年,朱孟依去了香港,并获得了香港永久居住证。这种变动无疑为以后合生创展在香港上市铺就了一条极易到达的捷径。
坊间传闻,朱孟依在广州的发迹得益于他在广州有着良好的政府关系。因而预知到了未来广州新城发展的契机,在这一年购下广州偏僻一隅的天河区大片农田。
因此,极具前瞻和超大气魄的朱孟依,在90年代初就奠定了以后财富几何级增长的牢固基础。
对于多数石狮商人而言,事业的起点从石狮开始,但石狮绝不是他们的终点。许荣茂的事业发展同样遵循了这条原则。
前面说到的许荣茂,1989年从香港回到石狮,其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就出现于此,他将手上的资金转了一个方向,投资房地产。一年内相继抛出了一连串的开发计划,使他迅速成为石狮地区最大的房地产投资商。据称,当时的投资回报率超过50%。
1990年,国内经济萎靡不振,坏消息接踵而至。许荣茂见形势复杂,生意发展空间受限,便决定移民。不久,举家迁到了澳大利亚,开始在悉尼和达尔文市投资房地产。
1990年
● 4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 原则上,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 5月,国务院下发《对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与国家土地管理局有关职能分工的意见》,对建设部部分职能作了如下定义:“建设部主管城市建设工作,负责城市的规划管理、房政管理与房地产业的行业管理,并根据城市规划实施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管理。”
● 8月,国务院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做出系统规定: 居住用地年限为70年;工业用地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年限为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年限为40年。
● 12月,建设部发布《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城市房地产产权管理较为系统的行政规章。该办法明确了“城市房屋的产权与该房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实行权利人一致的原则”。
第四章 冬天里的一把火
1991房企上市做大做强
斜倚祭坛,眺望你被荒烟染白的天际我倍感一种空前的虚无
因为我看出在你微笑后面隐藏着的悲哀也许这正是由于我平生多劫的缘故你更苦呀!我怎能不端起纯白的米酿洒向这块埋有一代代忠魂的黄土
——黑大春《祭》
“东欧剧变”让中国的改革者对改革开放有了更加强烈的紧迫感。1991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出现了下降。其时,国内尚未消弭两年前政治风波的阴影,西方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各种杂音此起彼伏,对改革开放的诘难也随之而来,并与坊间流言混杂成为舆论焦点。
世界风云变幻,中国向何处去?邓小平用他一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指出了90年代中国人应该怎样做。1991年春节,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过年。锦江春暖,世人有幸聆听一代伟人的精辟论述。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正如一份杂志的评论所言,伟人之所以伟大,往往在于说出了大家心里都明白的道理,大家都立即接受并付诸实施。
回望历史,今天如何感慨都不过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某些潜流真实地阻碍了中国改革开放向前走的步伐,1991年邓小平的声音,成为那个年代里的面对可能遭遇的一切困惑时披荆斩棘的利器,也奠定了中国平稳地度过了高速发展的90年代的思想基础。
春江水暖鸭先知。事实上,1991年最先感知到热量的是现在雄霸中国房地产江湖的大佬们。
1991年,对于中国房地产业来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成立,全国第二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确定城市土地转让制度正式实施。此后,国务院先后批复了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改总体方案,房改终于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大环境中拉开了大幕。
在全国的很多城市,1991年的房改大旗,标志着原来的房屋分配制度成为历史。这就直接带来了两个结果: 一是商品房需求量急速上升,房价开始攀升;二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特别是私营房地产企业)纷纷成立,标志着商品房开发的全面启动。
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有商品房的概念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如果今天从现代房地产发展史的角度正本清源的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应该从一个多世纪前的上海石库门算起。
19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上海设立租界。开始时,租界里住的全是外侨,后来战乱迫使江南富绅及中产阶级市民纷纷举家涌入租界寻求庇护,有人还在租界里盖起了房子。不久,租界当局下令取缔了这些有碍观瞻的建筑。这时,一些有眼光的商人依照租界当局的市容规划,借机大量修建住房,提供给这些外来人口居住。这些住房模仿欧洲联排房屋在营建与开发上的规范化,同时融合了江南民居中三合院住宅的空间布局与文化韵味,既符合占地少、设计合理、坚固耐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又适合市井平民的消费水平。所以,这种建筑模式在上海很快就风靡一时,甚至每年以数万计递增,逐渐成为上海市民欢迎的里弄建筑。这类中西合璧的住宅正大门以条石作门框,因而名为“石库门”。
随后,在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出现了石库门式的里弄住宅。
石库门作为建筑和文化的产物,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的出现是一种城市生活的必然。洋场风情的现代化生活,使庭院式大家庭传统生活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石库门弄堂文化。石库门里的“亭子间”、“客堂间”、“厢房”、“天井”以及“二房东”、“白相人嫂嫂”、“七十二家房客”等与石库门有关的名词成为老上海们温馨的记忆。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说,石库门是最有海派风情的民居建筑,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是上海城市精神与智慧的物质结晶。
我国的普通邮票第23组《中国民居》中的上海民居图案采用的就是石库门建筑。中国共产党也诞生在望志路(今兴业路76号)一幢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中。
上海石库门的开发、设计、建造和经营者是中国房地产开发的鼻祖,商品意义上的房地产概念就在那个时期的上海产生的。之前,中国人的房子一直是自己建造、自己居住的。
从1991年开始,上海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改造。在摧枯拉朽般的拆迁之中,如同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一样,上海的石库门也在成片消失,几乎每天都有弄堂被夷为平地。这些曾经承载过厚重历史的老建筑,在素享“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的上海的地图上正一天天减少。
随着城市的逐步发展,上海居民已淡化地域概念,一个个环境优美、风格别致的居住小区开始出现。但是,“住在弄堂怨弄堂,离开弄堂想弄堂”。看着已经风烛残年的破旧的石库门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一片片消失,许许多多在石库门的嘈杂和凌乱中出生、长大的上海人依然在里弄之中流连忘返,百感交集。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最稳健的房地产市场当属北京。
北京房地产市场,套用市场经济的一个名词,当时还是一个“寡头竞争”的时代。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北京大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北京城市改进综合开发总公司等几家具有深厚政府背景的房地产企业,“瓜分”了京城绝大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这些寡头企业的老总们,在谈笑间运作着数百万平方米、数十亿的大项目。从“量”的角度而言,这是后来者不得不“高山仰止”的。
现在的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叫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