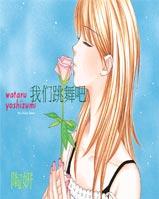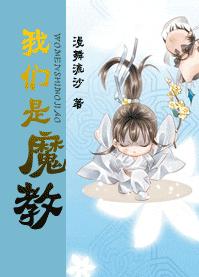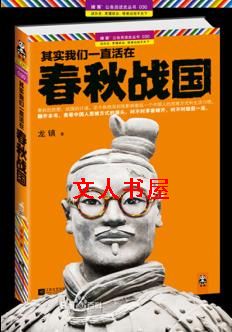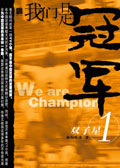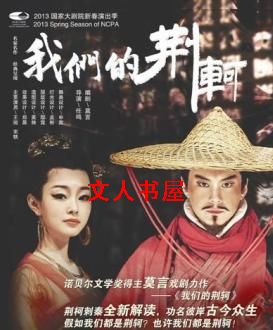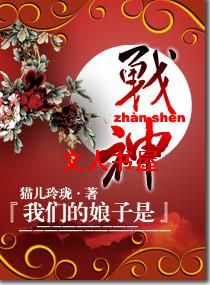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另一位叫冈田的《日本经济新闻》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在1978年夏天前来上海采访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里衣料和电器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而且居然有了自动售货机。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这年的秋天,一位叫保罗·马金迪的英国人也来到中国,这位日后红透欧洲的路透社记者采写的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些报道更富于人文色彩。
保罗·马金迪是从回归前的香港来到中国大陆的,他对香港列车能在早上9点提供杜松子酒或者冰镇威士忌显然感到满意。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保罗·马金迪只能喝到滚烫的茶水了,他注意到在这个招待外国人的车厢里,茶杯的装饰还是很精美的。
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后,保罗·马金迪对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的直接对比感到好奇。进入大陆的时候,香港的高楼大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绵延数里的起伏丘陵和种满谷物的庄稼地。在跨越罗浮桥的那一刻,保罗·马金迪感觉到了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强烈的好奇心。对于香港的拥挤来说,保罗·马金迪觉得这里的一切是祥和平静和妩媚动人的。但他想不到的是,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即将成为中国最有生气和最为繁忙的经济特区。
列车过了罗浮桥后,西方旅行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一位丹麦旅行者则把他的感受用录音带记录下来。
列车的终点站是广州站,在那里,保罗·马金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位20多岁眉目清秀的翻译彬彬有礼地对保罗·马金迪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去了那里。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1978年,也是一个有着太多期望的年份,压抑了许久的民众思想和停滞不前的国家经济都渴望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酝酿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
1978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同四川省领导谈话时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黑龙江、吉林、辽宁,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
16日,邓小平在吉林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还从政治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17日,邓小平在沈阳又尖锐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18日,邓小平在唐山再次发话:“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 中国已经等不起了!
是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心中正在勾画着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脑中思考着中国将来如何富强。
访问期间,邓小平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一场为世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让西方记者们充分领略了他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他说:“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22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谈到要承认落后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饶有趣味的话:“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这一尖刻的自我评价逗得记者们哄堂大笑,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态度正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希望所在。
在对日本八天的访问中,邓小平挤出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这次访问,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
在访日之前,邓小平就来到了新加坡。据李光耀回忆说,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这种标准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发展上的。
邓小平本来是要进入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考察,但由于安全原因未能如愿。于是,有关方面安排他到新加坡住房发展局听取范德安局长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最后他登上该局22层办公大厦顶层,满心遗憾地鸟瞰了下面的住宅小区。
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邓小平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以派人出来看嘛,学习人家是怎么搞的。“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随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施燕华回忆说,要回国那天,她正在收拾行李,突然邓办主任王瑞林走进来说:“小施快准备一下,首长要看看你住的房子。”
邓小平来到这个普通房间,认真地看了房间的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最后自言自语地说:“很好,安排得很合理。”
施燕华说,在新加坡的这两天,邓小平很少讲话或者评论他见到的新事物,但新加坡之行显然让他有所心得。
冰河解冻,大地回暖。
这一年,一切似乎都水到渠成。
1978年能够被史学家记录或者被坊间认为标志性的时间点,与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11月至12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达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5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排除干扰,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中国改革的伟大决策。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作为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当时的中国寻求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迎来了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大国家的春天。
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个冬天,15岁的潘石屹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山沟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这位“身不高,体不壮”的农民后代,在20多年后成为中国房地产界的大腕,资产达数百亿元。
潘石屹坦陈自己“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享过改革的福”。他说,不是邓小平,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只能是一个终老困苦于山沟沟的农民。在中国,有同样经历和想法的,又何止潘石屹一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让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暖洋洋的。因为,从此中国重新回归于理性而正确的轨道上。
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这个经历了千年风雨激荡的东方古国校准了定位,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中国历史上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留下最富忧国忧民情操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居者有其屋,多少年,多少人,在为这个梦想而努力,房子始终倾注着人们的无限希冀与憧憬。千百年来,人们对住房的追求从未间断。华裔学者杜维明曾把中国的住房比喻成一部最缠绵的红“楼”梦。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人却是“居者忧其屋”。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住房极其紧张的“特困户”,甚至无处栖居,流落街头。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汇,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小、太挤。
上海的冬天,阴沉沉的、灰蒙蒙的,无精打采的太阳将它缺乏热量的光线投射到这座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狭窄的里弄和蠕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投射到拥挤的楼房和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上。
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就是这些“鸽子笼”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三口人。
3。6平方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上下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30年前,我们一家十口人就挤在位于永安里的20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中。”回忆起30多年前的情景,北京居民朱奶奶记忆犹新,一家十口人,除了七个儿女外,朱奶奶的婆婆也住在这个大家庭里。
20世纪70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还基本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据朱奶奶回忆,当时的福利分房依据的是职工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等综合评分。“想分房要论资排辈。”所有人都期盼着单位分房能尽快轮上自己。但是单位分房的情景更是让朱奶奶至今难忘:“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送礼的、递条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胁的。经常有要结婚的年轻人,跑到有关部门吵着闹着要求分房子。”
60年代末出生的张强小时候和姐姐、父母在筒子楼里居住,直到他上了初中,单位才给父亲分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带独立洗手间的房子,虽然位置比较偏僻,但比起一家四口挤在不到30平方米的筒子楼里,条件改善了很多。张强至今还记得搬进新家的当天晚上,一家人很奢侈地到餐馆庆祝。
事实上,在福利分房时期,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能在退休前分得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旦儿女成家,就只能与父母挤住在一起,三代同屋的住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众多家庭之中。
过道上码放的煤球,用废旧木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嘈杂的公共厨房、水房,潮湿阴暗的过道,昏黄模糊的灯影……至今;筒子楼里的记忆仍然深深地印在张强的脑海中。
统计数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标杆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仅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刚刚新中国成立时少了0。9平方米,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新中国经济观念中,普通职工的住房需求,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视的,本应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被用来发展重工业。
然而,面对全国869万城镇缺房户,疲弱的国家财政早已无力承担。名义上用于房屋维修、管理、建造之用的由职工缴纳的房租,在低工资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怜。杨希鸿记得,在她每个月工资是40元的时候,她只需要交纳每平方米0。2元的房租,而且这个数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增加过。
房子一直是中国人烦恼的主题。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到1978年增加到9亿。1949年我国人均居住面积是4。5平方米,1978下降到3。6平方米。这还不包括城市逾1000多万尚未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假如把他们算上可能连3平方米都不到。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可想而知人们居住条件越来越差只能是唯一的结果。
据杨绛先生回忆,1977年她和钱钟书住在学部办公室已近三年,“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