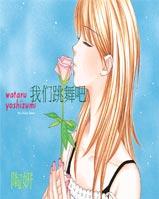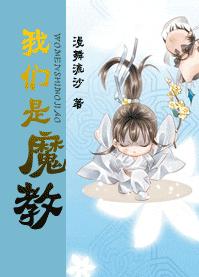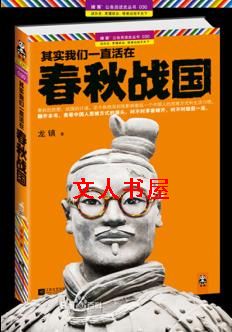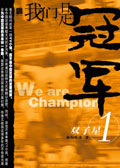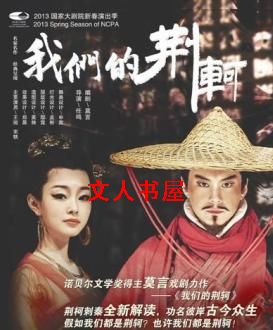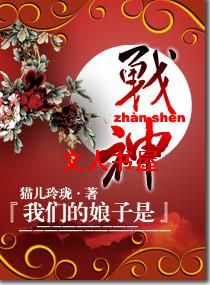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广东省国土厅、一些兄弟城市的土地局有关负责人到会,会议的议题主要就是研讨深圳的改革方案是否可行,是否可操作。在论证会上,香港戴德梁行主席梁振英提出:“方案是可行的,但必须修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否则外商是绝对不敢来买地的。”
无论如何,宪法问题是个大难题。而推动宪法的修改在当时看来,不啻为“奢望”。按照当时的规定,修改《宪法》需要30个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才有提案权,而当时深圳只有五名全国人大代表,连提案权都没有。
1987年10月中旬,中国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深圳迎宾馆六号楼召开。为改革找到理论上的根据,是深圳组织这次会议的初衷,但世事难料,到会的全是搞理论的名家,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党校都有人前来参加。这些专家大多带着研究生一起来。会上老师、学生分成两派,老师基本上对改革持反对态度,研究生持肯定态度的较多。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土地有没有价值,如果没有价值怎么会有价格?《资本论》一页一页地翻着找根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
1987年10月27日汇编的《深圳体改简报》里记录了这次研讨会的一些详细内容:“一种意见认为,地球本体是自然物,非人类劳动所能创造,并无人类劳动凝结。土地没有价值,不是商品。此外,《宪法》规定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买卖、出租、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转让都是不合法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土地是商品,因为土地凝结了人类劳动,比如说土地上的‘七通一平’;此外直接物化在某块土地上的劳动量仅仅是衡量土地价值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从社会总价值量中转移而来与土地结合而成的价值,而且往往与直接物化在该地的劳动量无关。改革本身具有超前性,包括理论与实践的超前,不应回避矛盾,受制于现行某些法规。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现行法律中的部分条款做适当的修改。”
而事实胜于雄辩,深圳的代表在发言中说道:“大家一直在争论关于土地是不是商品、有没有价值的问题。可我们在现实中无论是协议还是招标,把钱都收上来了,你们说它有没有价值?”
争论归争论,该做的还要做。好时光,不等人!此前深圳刚刚极其低调地通过协议、招标方式有偿有限期出让了两块土地。
9月8日,深圳市首次以协议方式有偿出让土地。这块地位于振华、中航交叉路口,面积5300余平方米,土地用于建单身职工宿舍。中航工贸中心以议标的形式成交,成交价106万元。签字以后即交付21万元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履行后,抵作地价。地价余款,中航工贸中心在30天内向政府一次付清。按合同要求,中航必须在1989年3月1日前完工。合同书规定,这块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
9月11日,深圳市第一次以招标形式出让第二块国有土地。深华工程开发公司在九家投标公司的激烈竞争中获胜,它以合理的土地标价、良好的建筑规划方案和企业资信取得一块46355平方米住宅用地,为期50年的使用权。该地块位于罗湖区深南东路南侧、北斗路东侧,旧名牛屎湖。两年后,今天的“文华花园”在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
11月,国务院批准国家土地局的报告,确定深圳、上海、珠海、广州、天津、厦门、福州等城市为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城市。由此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正式实施。
深圳市委、市政府立即决定再跨一大步,举行公开拍卖。
300多年前,英国人威廉·佩第爵士留下一句经典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
300多年后——1987年末,在中国特区深圳,首次揭开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的面纱。
这是一次酝酿已久的拍卖,这是一次让全世界都瞪大了眼睛的拍卖。
历史将永久记住这一天: 1987年12月1日。深圳人敲响了土地拍卖的槌声,中国土地市场瞬间发生“惊天”之变。这一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人们足足等了38年!这场拍卖,破天荒地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对传统土地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引起了国内外极大关注。
那是个晴朗的下午,深圳会堂7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下至28位香港企业家及数位经济学家亲临拍卖现场。中外20多家新闻媒体的60多位记者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多数香港人对普通话还不熟悉,拍卖采取了“双语”,主拍卖官、时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的刘佳胜讲普通话,副拍卖官、时任深圳市政府基建办综合处副处长的廖永鉴讲粤语。
刘佳胜后来回忆说:“如此高规格的土地拍卖仪式,后无来者。”
刘佳胜首先介绍了拍卖地的有关情况,这块编号H4094的地块紧靠风景秀丽的深圳水库,面积8588平方米,规划为住宅用地,使用年限50年。深圳市政府事先在报纸上刊登了《土地竞投公告》。拍卖前三天,已有43家企业领取了正式编号参加竞投,其中外资企业9家。
拍卖就要开始了,中航工贸中心的一位干部领着他的助手匆匆跑进了深圳会堂:“才看到报纸,来晚了。我们也要参加。”这位干部成了这次土地使用权拍卖的最后一位领取应价牌的竞争者。他的应价牌编号是: 44。
“土地使用权拍卖击槌器”是这次拍卖活动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局”,这只枣红色的做工相当精致的击槌器,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1987年12月1日。”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刘绍钧先生说:“这是专门从英国定做的,我们镶上这块铜牌,以记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如今,这只枣红色的小木槌静静地躺在深圳市博物馆里,它身上“1987年12月1日”字样,显示着它不同凡响的身世。
紧张、激烈的角逐出现在4点30分,刘佳胜、廖永鉴分别用普通话和粤语喊出了拍卖底价: 200万,每口加价5万元。话音未落,各竞投企业的法人代表争相出了白底并标有红色编号的应价牌。“205万!”“210万!”……会场四处几十块应价牌齐刷刷地举起来。
有人等不及了,“呼”地一下站起来,响亮地喊出了“250万”。会场气氛顿时爆棚。地价很快上升到390万。场内突然出奇的安静。片刻,市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的代表大声喊出:“400万!”场内爆发出一片掌声。
“420万!”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坐在那里笑眯眯地举起了11号应价牌。又是掌声一片。
随即,“430万”、“440万”、“450万”!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报价已升至520万元。此时全场鸦雀无声,眼看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就在主持人准备击槌时,场中又爆出一声:“525万”,这是骆锦星的声音。全场稍稍骚动后,又回到了平静。
“时间到!”刘佳胜一槌敲下,拍卖成交。沸腾的掌声淹没了拍卖官的声音。摄影镜头的闪光灯频频闪起,历史性的镜头此刻凝住。
深圳,也是全国,首块土地50年使用权通过拍卖的形式以当时的天价找到了主人。
深圳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意义不仅仅是它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土地收入。它的意义更在于,一向被人们视作是资本主义专利的市场机制,已开始在中国土地配置和使用上发挥作用,土地也开始在流动的过程中得到了增值。有人说,整个拍卖时间虽然只持续了17分钟,但这是为此后深圳开创出“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础的17分钟,也是整个中国迎来土地真正成为“黄金”时代的17分钟。
第二天,国内和香港各大报纸差不多均在头版报道:“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空前壮举,也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新时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里程碑。”
深圳敲响了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槌”,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的惊天第一拍,开创了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先河,这是中国土地管理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直接刺激了深圳乃至全国的土地拍卖市场,引发了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革命。
至今,那一天深圳会堂的轰动场面在骆锦星脑海里依然清晰。
“我们虽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事先进行了预算,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研究一致认为,这块地志在必得,可以接受的底价是530万。但是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还是让人始料不及。”
骆锦星为中国土地第一拍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此后不到一年,深圳特房公司在这块土地上建起的东晓花园,一共151套住宅一小时内售罄。房价是每平方米1600元,远远低于当时的市价。尽管如此低价,公司还是净赚了400万元。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东晓花园第一批住户已经所剩无几,小区的名气和地位早已被后起的高档小区所取代。即使是在小区门口,问起东晓花园的显赫身世,也不再有多少人知道。
多年来,深圳方面声称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建议来自一位知名人士,具体姓名没有点破。一直到2006年10月,83岁的霍英东逝世,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接受记者采访,讲述霍英东为深圳作出的贡献:“在深圳发展最需要资金的时候,霍英东给当时的市领导提出了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为政府增加收入的建议,从而使深圳也使全国有了首次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石破天惊之举,此举直接促进了宪法及相关法律在土地使用权问题上的修改。”
1987年12月底,《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出台。次年年底,广东省人大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
与土地使用权拍卖相联系,深圳开始筹划推出住房制度改革,1987年9月22日,深圳市政府开始特区住房调查。1988年6月10日,市委、市政府在深圳会堂举行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宣布深圳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出台。
仅仅两个多月后,福州敲响了“第二槌”。1988年2月11日上午,福州以458万元成功拍出五四路一幅写字楼用地,这是国内首次向外商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不久,8月8日,上海虹桥开发区26号地块有偿出让的国际招投标项目也尘埃落定,日本孙氏企业有限公司以2805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该地块1。29公顷50年的土地使用权。
4个月后,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例,将原来《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并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接着,《土地管理法》也按此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的禁锢终于完全放开。
“这是一次历史性突破,是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标志着我国的根本大法承认了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属性,跨出了土地商品化、市场化的重大一步。”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说。
房地产专家、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平认为,这是中国土地商品化的历史性突破,没有那“一拍”、“一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时,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政策的推行,实现了国家对城市土地所有权使用的经济价值,同时,为土地这一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奠定了政策基础,也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出了贡献。
不过,王平指出,虽然有了“一拍”、“一改”,但从1987年直到2001年国家住房货币化改革之前,深圳的土地拍卖进展并不顺利。据《1997年深圳房地产年鉴》显示,截至1996年底,深圳市国土部门共签订出让的3615宗土地中,协议出让占到75%,招标只占3。3%,拍卖仅占0 7%。从1987—1998年11年间,深圳通过拍卖出让的土地仅有7宗。与2001年后每年都超过10宗拍卖地相比,有天壤之别。
仿佛是和南方经济特区深圳遥相呼应,北方海滨城市烟台在1987年率先打响了全国房改“第一枪”。
新年第一天,烟台市住房制度改革开始模拟运行。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第二天,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自1987年起,各地区的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1985年,结束长达近20年在电子工业领域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工作生涯后,俞正声就任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