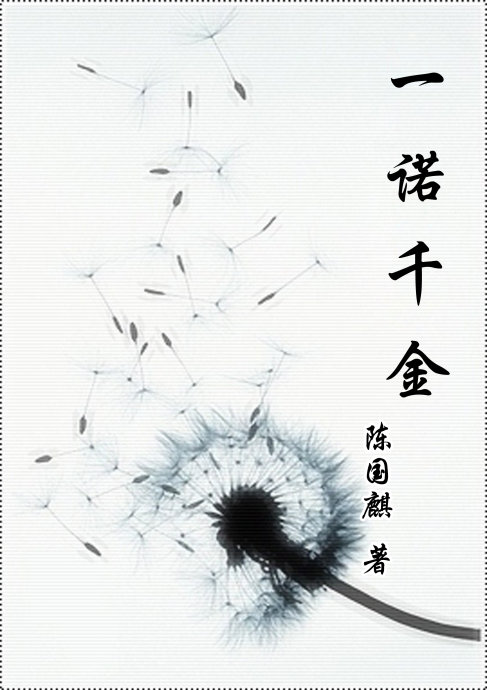我婚礼那天早晨,阳光明媚而温暖。一切都很顺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来临了。我穿着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美丽的绸缎衣服,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 然而,就在这时,醉熏熏的父亲东倒西歪的向我走来。是的,这个时刻,每个新娘是不能没有父亲的挽着她的手,把她亲手交给新郎的。父亲嘴里呼出的烈酒熏得我几乎窒息,他伸出手挽起我的胳膊时竟险些跌倒。与此同时,《婚礼进行曲》响起来了——是迈步向前走的时候了。 我极力掩饰,装出美丽的微笑,用尽全力支撑着我的父亲,不让他倒下。本来应该是父亲挽着我,可现在是我在架着他的身体向前走。他每走一步都踩在我长裙的下摆上,让我不断地和他一起出丑。等到我握着新郎的手站在圣坛上,对我来说,婚礼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给败坏掉了。我生气,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天哪!那一刻我决定永远不原谅我的父亲。...
** 《一路走来一路读》 作者:林达 第一部分 走路(一)上帝安排的通信(1) 昆西,是一个听着耳熟的词。它是一个地名,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昆西海湾;它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小镇在昆西海湾的南岸,因海湾而得名,距离波士顿只有7英里;它也是一个人名,因诞生在昆西小镇,就由同样诞生在这里的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们父子又使得小城名扬美国,声名甚至超出了美国。在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父子总统——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昆西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对于外来的旅行者,它几乎在竭力满足你所有的期待: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宁静的住宅街区,和浪花拍打着的海岸风景。除了亚当斯父子,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大陆会议主席,而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真正的第一总统”的约翰·汉考克,也诞生在这里。所以,昆西也被人们称作“总统城”。在他们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逃难的人流中,一位母亲带着她3岁的孩子,随着人流向远方走去。 这位母亲把最后的一点干粮磨碎,喂给孩子吃,看着孩子瘦弱的小脸,禁不住落下泪来。她知道,自己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半个月的饥寒交迫,令她的身子极为虚弱。她怕自己支撑不住,最后孩子也无法活命。想来想去,这位母亲抱着孩子走到一位逃难的人面前。这个人,是她家以前的邻居,是个医生,为人非常善良,她知道,如果现在把孩子托付给他,他一定会把孩子养大成人。 “我一辈子感激你,”母亲给这位邻居跪下了,“请您带着我的孩子一起逃命。” “不,我不能答应你。”邻居为她和孩子简单地检查了身体状况后,拒绝了她,“我的事情已经够麻烦了,我帮不了你的忙。”...
**(一) 冯苇一在大马路上匆匆地走着。这时已是傍晚时分,街市在转暗的光线下渐渐热闹起来,他最近的心情可以说是糟透了,可是热闹的市井还是那么热闹,根本不理会他的心情。 冯苇一在找一个人,一个叫阿辉的人。 阿辉曾经是他的好友,两年前两个人合力打造一家小公司,由于厌烦复杂的手续,便用了阿辉姐姐的待业证办理。总算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公司有了一些正常业务,虽说每一单的营业额不大,但是稳稳妥妥算是一盘正经生意在手,慢慢做不信就不能做大做好。结果突然有一天,苇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阿辉竟然背着他卖掉公司,人间蒸发了。 一开始,冯苇一的同居女友商晓燕还帮着他一块找阿辉,两人同声同气要劈了阿辉。后来实在找不到阿辉和他姐姐,晓燕就转过弯子来劝冯苇一面对现实。苇一不肯,非要找到阿辉不可。晓燕说,这件事你不愿意报案,又一定要找到他,你到底想怎么样?苇一说我要亲口问一问他是怎么想的...
**《放下武器 》许春樵 《放下武器 》许春樵 简介 《放下武器 》许春樵 1 城市的烦燥不安从早晨就开始了。琐碎的自行车铃声灌满了大街小巷,密集的汽车拥挤着爬行在举步维艰的道路上,尾部冒出了断断续续的黑烟,一些暗藏的烟囱以固定的姿势继续喷吐着由来已久的工业灰烬,烟囱下面是灰烬一样稠密的人群蠕动在稀薄的光线里,他们来去匆匆,去向不明。 太阳早就升起来了,是个睛天,但天空灰蒙蒙的,感觉到四处弥漫着浑沌的阳光,抬起头却怎么也看不出阳光是从哪里铺到地面来的,这种别扭的感觉很像是一个穷人无缘无故地接受了一笔来路不明的捐款。于是我的目光开始关注路面上扬起的灰尘和匆匆经过的形形色色的鞋子,当人们走在路上时,鞋子里就装满了思想和动机。...
『状态:全本』『内容简介: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1989年9月5日,是周扬的追悼会。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同一个人默哀,虽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经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追悼会,能像他的追悼会这样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同时负载着众多难以解析』**章节内容开始-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1989年9月5日,是周扬的追悼会。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同一个人默哀,虽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经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追悼会,能像他的追悼会这样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同时负载着众多难以解析的矛盾。...
美国大选期间,我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报道,说的是某县选举委员会怎样处理老人院里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的投票问题。众所周知,美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很多美国老人生活在养老院里。虽然老人们不再活跃在社会活动舞台上,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却曾经经历过二战,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统计表明,投票率最高的是60岁左右的老人,最低的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所以,老人投票一向为政治家们所重视。可是,如果老人很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他们怎么投票呢? 通常,这些老人受优待,不必亲自去投票站,而是通过邮局把选票寄来,老人们填写了再寄回去。可是,有些老人连做到这些都困难了,比如这则报道里说的,老人院里身患“埃兹海默症”,即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该怎么办呢?...
我今天想讲的是年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今天你们大概20岁,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25年之后,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已72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文学: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为什么需要文学?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我想,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
屋子里静得可怕,墙上滴答滴答的钟声,在她听来是如此的惊心动魄,床上的母亲,双目沉陷,气若游丝。 她紧紧握住那只枯槁的手,她要让母亲感到女儿对她永远的依恋与不舍。然而,母亲依然是清醒的,她微微颤动着双唇,视线将女儿引向墙角的一只老式衣柜。女儿的心猛的抽搐起来,一大颗冰凉的泪跌落下来。她明白母亲的意思。 20年来,刀一样刻在女儿的心坎上,怎能忘却呢!那天母亲喘着气在病榻上,一字一句的对女儿交代后事:我一生再无它求,只求你们子女一件事,我死后,随便葬在哪里,但将来决不许与你父亲葬在一起,那时,她怎么也没料到母亲对父亲竟有如此伸的怨恨。所辛,后来母亲从死神身边回来了。她这个女儿才有机会探听到母亲的心音,其实,他们夫妻两是一对怨偶,那年她去探望丈夫,竟发现了他与一女子相好同宿,当时他在妻子面前表示要痛改前非。后来,丈夫落实政策回来了,但是,她发现丈夫还在和那女子联系...
:**钱学森传王寿云 等钱学森(一)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名家治,后以号行)是浙江杭州一没落丝商第二子,少小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曾到日本学教育和地理、历史。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女儿。钱学森的外祖父欣赏钱均夫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民国成立后,钱均夫就职北京当时的教育部。钱学森在3岁时随父到了北京,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师大附小和师大附中。...
作者:燕山雪** 奔腾的黄河两岸,黄土高原静默着,如同千百年来一直静默着的中国农民的群雕像,任凭母亲河年复一年地从自己的身上割削去大块大块的血肉。我像一个吟游诗人一般在华夏的山河间四处游历,让自己沾染天地万物的灵气和生气,一边采撷诗和歌的种子。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深深感到南方的山水太过秀气,只适合赏玩。漓江的水声如同刘三姐的山歌般动人,却也只是刘三姐般的村姑而已。而当我真正坐着一叶小舟出没于黄河的风浪中时,在黄河洪大的涛声中,我分明听见了无数喉咙在呐喊。 这呐喊声从远古一直回响到今天,有盘古开天辟地时的那声怒吼,也有神农收获第一粒稻米时的欢歌;有大禹治水时的劳动号子,也有长城脚下千万尸骨的...
1 从一个朋友的嘴里,我知道了这样一则故事:说从前有一家人,门前长了一颗树,这棵树年高德劭、枝叶繁茂,十分喜爱这家人的一个小孩。这小孩饿了,他就让他摘果实;小孩渴了,他就叫他嚼叶子。夏天,他给小孩遮凉;冬天,他给小孩挡雪。等小孩长大的时候,他又让他把枝叶割下来,编成一个花冠,送给他心爱的姑娘。 这样过了好多年,这少年娶妻生子,变得很富有。有一天来到大树旁,说:我已厌倦了现在的生活,我要到远方去,请你让我锯下你的树干,打造一条大船。树听了很忧伤,但忧伤的不是这冷酷的要求,而是他就要有很长时间见不到这少年了。 就这样,少年驾船走了。过了好多年,一个老人步履蹒跚,来到他面前说,我就是那少年,我已疲惫不堪,需要休息。树说,很好,我已苦苦地等了你几十年,幸亏我还有一个树桩可以做你的坐垫。老人又拿起斧头砍倒树桩,做了一把躺椅。...
从西安回来,我把这个故事讲个别人。别人都于我有同感,很愤怒。可是文章写到这时,我的疑问出来了:管理局禁止老头吹笛好像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老头确有卖艺之嫌。否则,他至少应该让一让再收那20元钱,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收钱;第二,怎么一切都像排练好似的,有惊无险,显然老头充分利用了我们这样游客的猎奇心,同情心和“正义感”;第三,老头好像很怕管理人员,其实他不怕,如果真怕就不会带笛子来,更不会在管理员眼皮底下吹。他原来同管理员玩得是痞子游击战——我反正身无长物,不怕罚,不怕抓。 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卖艺,有何不可?管理局可以收管理费,老头可以增加收入,游人可以娱乐,皆大欢喜。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此,卖艺这别处可以,在华山不行,因为华山只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大部分窄的只能勉强通过两人。因此,在游人如织的华山上,如果出现堵塞,是很危险的,华山管理局不让卖艺的这条规定是...
每次他来 ,脸上都带着一种谦恭、讨好的表情,他低三下四,和每个人打招呼,不停地说着谢谢。是的,他感谢我们,更确切地说,他感谢的是我们所代表的国家机构和一种保障机制,这种保障机制使他每月能在我们手中领到100元钱。他矮小、干瘪,面容总带有一种病态的赤红。每次看到他,我都能感觉到一种衰败的气息,那是一种被生活打败了的气 息。他下了岗,妻子没有工作,女儿上初中,他是城市里赤贫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什么都干,卖菜、卖内裤、卖袜子一次在路边,风将他的袜子吹向了排污沟,他下水去捞,被玻璃削去了半个脚趾,他没心疼自已的脚趾,却庆幸自已捞上了袜子。没有人会为他每月领这100元钱而有异议,是的,他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需要帮助的对象。...
他和她的故事是我所遇见的最迷人最深刻最忧伤最宽广的爱情。 他说她的人生经历了两次黑色的秋天,一次是含冤被打为“右派”,一次就是现在。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席葬礼。第一次来到被叫做殡仪馆的地方。 早晨7点,我就乘车来到了这里,这儿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工厂,只是大门口一个阴森的“奠”字直慑人心,让我下意识地提一口气,抓紧了黑色的连衣长裙的下摆。我一步步地朝那堆有我熟悉的,也有完全没有见过的。我看到我熟悉的那些人全部穿着统一的黑色,有种古怪的感觉。 爸爸说:“我们去看一看卫生和化妆的工作做好了没有,你一个人就去陪陪他吧。”顺着他手指向的方向我看到了一个清瘦的老人失神地坐在台阶上。那是死者已经七十几岁的丈夫。我点了点头,安静地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轻轻地握住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