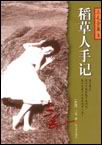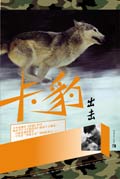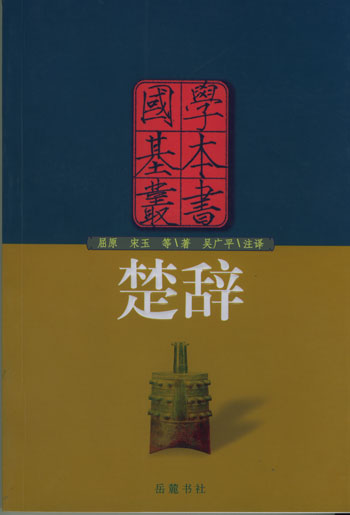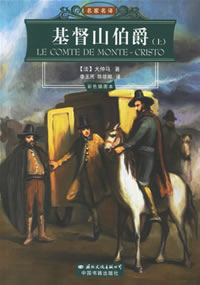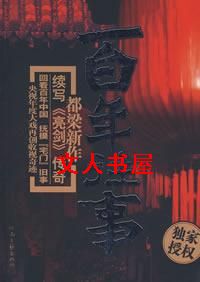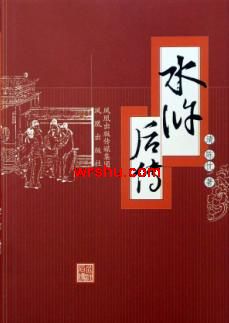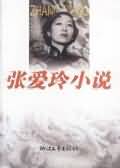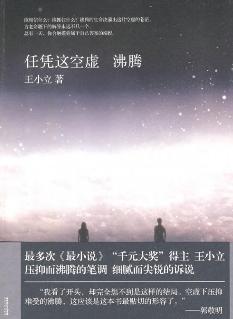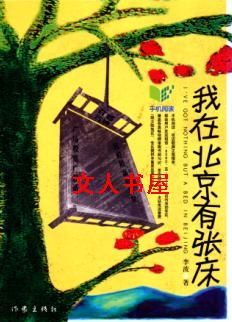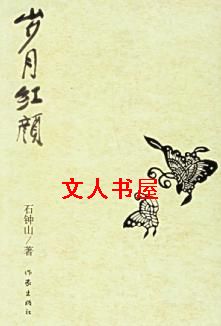作者:张铭 王峰《卡豹出击》:感动,因为纯粹当卡豹在深山密林中一遍又一遍地来回奔波,当卡豹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向一条所谓的“英雄之路”迈进的时候,它知道,有一个人在不远处等待着它。他们相互信任、相依为命、不离不弃。甚至最后,它等着那个人带着生命之水来救它,它怀着“他一定会来”的信仰等待,一直等待,然后安详地死去。它和他,像亲人、像朋友、像恋人一般地爱着。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把《卡豹出击》介绍给朋友,问他们有何感想。他们说:“感动。”我问为什么,他们回答:“因为纯粹。”我被这个答案震慑住了。我想起几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上面写道:如果纯粹,你便是朝圣者,如果不,那你仅仅是个勇士。我知道,《卡豹出击》传达给我们一种久违的纯粹的爱。这种爱,让卡豹看起来有朝圣者般的光彩。而我们,被这种爱感动了!因为缺失而稀有,因为稀有而感叹,因为感叹而感动。...
作者:[法]大仲马第一章 船到马赛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避风堰了望塔上的了望员向人们发出了信号,告之三桅帆船法老号到了。它是从士麦拿出发经过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立刻一位领港员被派出去,绕过伊夫堡,在摩琴海岬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了船。圣·琪安海岛的平台上即刻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艘大船的进港终究是一件大事,尤其是象法老号这样的大船,船主是本地人,船又是在佛喜造船厂里建造装配的,因而就特别引人注目。法老号渐渐驶近了,它已顺利通过了卡拉沙林岛和杰罗斯岛之间由几次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海峡,绕过波米琪岛,驶近了港口。尽管船上扯起了三张主桅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桅帆,但它驶得非常缓慢,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岸上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于是互相探问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不过那些航海行家们一眼就看出,假如的确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一定...
作者:(清)陈忱出版说明《水浒后传》是《水浒传》的续书,讲述梁山泊劫后幸存的李俊、阮小七、李应、燕青等英雄,再度聚啸山林,反对奸臣恶霸,抗击金兵入侵,最后到海岛创基立业的故事。《水浒后传》旧题“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现存最早的康熙甲辰(1664)本内封上刻有“元人遗本”,下有一段文字:“宋遗民不知何许人,太约与施(耐庵)、罗(贯中)同时,特姓名弗传,故其书亦湮没不彰耳……”其实“古宋遗民”、“元人遗本”都是托词,真实作者乃是号雁宕山樵的明遗民陈忱。陈忱(1615—?)字遐心,一字敬夫,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自幼好博览群书,经史之外,稗说野乘,无不涉猎。据他自己说,年轻时,曾寄居野寺,“篝灯夜读,情与境会,辄动吟机,眠餐不废者三年”,然后出游福建、两广、湖南,“凡四易星霜”。明亡时,他正值盛年,面对家破国亡、江山易代的巨变,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感情,以明遗民自居,绝...
作者:张爱玲赛姆生太太是中国人。她的第三个丈夫是英国人,名唤汤姆生,但是他不准她使用他的姓氏,另赠了她这个相仿的名字。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来,赛姆生太太曾经结婚多次,可是从律师的观点看来,她始终未曾出嫁。我初次见到赛姆生太太的时候,她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那一天,是傍晚的时候,我到戏院里买票去,下午的音乐会还没散场,里面金鼓齐鸣,冗长繁重的交响乐正到了最后的高潮,只听得风狂雨骤,一阵紧似一阵,天昏地暗压将下来。仿佛有百十辆火车,呜呜放着汽,开足了马力,齐齐向这边冲过来,车上满载摇旗呐喊的人,空中大放焰火,地上花炮乱飞,也不知庆祝些什么,欢喜些什么。欢喜到了极处,又有一种凶犷的悲哀,凡哑林的弦子紧紧绞着,绞着,绞得扭麻花似的,许多凡哑林出力交缠,挤榨,哗哗流下千古的哀愁;流入音乐的总汇中,便乱了头绪——作曲子的人编到末了,想是发疯了,全然没有曲调可言,只把一个个单独...
作者:刘儒一、赴任太城县又一个县委书记下台了!这是该县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第三个书记遭此下场。县里县外议论纷纷,都说三个书记的下台皆因一个女人的关系。英雄难过美人关,看来真是一点不假,三个书记竟无一人闯过去,全部败在那个女人的石榴裙下,实在是可叹、可悲呀!但不知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回曰:是也;非也。说是,因为三个书记的免职调离确实和那个女人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当了书记以后,和那个女人的桃色新闻一个比一个多,一个比一个邪乎,全都有根,有校,有叶儿,哪个酸,哪个浪荡风流,哪个叫人笑破肚皮,叫人指脊梁吐唾沫的情景儿,真是不堪人耳。因此,他们一个个名声扫地,全县工作出现混乱的状态,告状信像雪片一样落在地区领导的办公桌上。为了顾全工作大局,地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接连做出免职调离的决定。...
作者:张纯如****************第一部分***************---------------序(1)---------------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对日本而言,占领南京是战争中决定性的转折点,是日军在半年里同蒋介石的军队在长江一带厮杀的胜利的顶点。而对中国军队而言,英勇的上海保卫战最终失败,最优秀的部队也伤亡惨重,而南京的陷落则是一次惨痛的,或许是致命的失败。 现在看来,我们还可以把南京当做另一种类型的转折点。南京古老的城墙里发生的一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收复南京,赶走侵略者的决心。中国政府撤退并重组,最终在这场于1945年结束的战争中击败了日本。在其问8年中,日本占领着南京,并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人中的投降分子组成的政府;但这个政府从不具可信性和合法性,它也从未能使中国投降。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南京的暴行使公众舆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对日本。...
作者:钱刚*第一章蒙难日“七·二八”地震发生后的唐山市区历史将永远铭记地球的这一个坐标: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人类将永远铭记历史的这一个时刻:公元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53.8秒。仅仅在一秒钟以前,地球的表面似乎还是平静的。在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一切都和往日一样,夜阑人寂,大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开滦矿务局唐山矿的高高的井架上,天轮还在以惯常的速度旋转;新落成的开滦医院七层大楼,透出几处宁静而柔和的灯光。整座城市在安宁地熟睡。某机关宿舍中,一位名叫蒋红春的女中学生,在屋里打完驱赶蚊虫的“滴滴涕”,刚刚回到床上;河北矿冶学院干部陆延麟担心有雨,刚刚起来收下晾在窗外的衣服;火车站服务员张克英正和一位工友商量买夜餐的事;一位名叫刘勋的大夫,因有急诊,刚刚披上外衣走出屋子……...
作者:王小立该相信什么?该抓住什么?沸腾的生命浇灌出这片空虚的苍茫。古老命题下的答案永远不止一个。总有一天,你会触摸到属于自己答案的端倪。任凭这空虚沸腾BR IM OVE R WI T H TO MF OO L E RYOCR BY 猫小白很白 MAY THE LORD HAVE MERCY ON MY SOUL有我知道。有我记得。便已经足够。楔子“最近还忙着练球吗?”我将手机光标移进通讯簿的名单,选中其中某个名字,将这条短信发送过去。一个小时之后,我收到对方的回信:“你是”。他回。扼要的两个字,连后缀的问号都懒得打上。我撇着嘴对着手机屏注视了两秒,听见自己的手机在删除短信时,发出的细微而干脆的提示音。“嗒”。又是无聊的一天。...
作者:李波【】自序丑话说在前面(自序)我生活在美国大湖区一个美若仙境的城市,几年难见一个汉字,偶遇一同胞也不咋说中文,除了联系国内或梦中呓语根本用不上母语。有时梦中惊醒,忘着枕边太太雕塑般宁静的西方人脸孔,突然想到——会不会哪天我也像鸵鸟翅膀蜕化一样丧失母语能力?这种不可名状的异域感、异化感和异物入侵感让我不寒而栗。我开始和自己说话,关照过往的生活。记忆像微量重金属一样沉淀在血脉里,身处异域也难以排遣。流浪是一种存在(只要你在地球上),无论你爱它,还是恨它,都铸为生命密码融你一体——正如困兽犹斗的八年京漂,结束于四年前,至今碾盘一样压碎我的梦境。然而出土一段生活——即便蚀骨铭心——也难免粘土带灰,面目可疑。迄今为止的人类进化,记忆密码还无法数字化储存,这世界没有高保真的历史,即使历史就在昨天。尤其一旦叙述涉及当事人,皮囊下的名缰利锁、损人肥己、文过饰非、避重就轻...
小时代 (第一季完结版)Chapter1---Chapter10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与时代》,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都会--留下他们的眼泪。拎着LV的年轻白领从地铁站嘈杂的人群里用力地挤出来,踩着10cm的高跟鞋飞快地冲上台阶,捂着鼻子从衣裳褴褛的乞丐身边翻着白眼跑过去。写字楼的走廊里,坐着排成长队的面试的人群。星巴克里无数东方的面孔匆忙地拿起外带的咖啡袋子推开玻璃门扬长而去,一半拿出咖啡匆忙喝掉,一半小心拎着赶往老板的办公室,与之相对的是坐在里面的悠闲的西方面孔,眯着眼睛看着《shanghai daily》,或者拿着手机大声地笑道"What about your holiday?"...
作者:石钟山【由文,】岁月红颜1下乡三年的知识青年李红梅,在那年大雪封门的日子里,爱上了本地青年何二宝。这大约是李红梅的初恋,也是她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恋爱,从此,她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李红梅生长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红梅在那座黑糊糊的城市里结束了自己并不令人怀念的学生时代。在上学的时候,她差不多就把自己未来的命运想好了。毕业后,她会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去上山下乡,这是他们这代人共同的命运。也有少数幸运者,从学校直接去当兵或者留在城里,接父亲或母亲的班,成为一名工人。她知道自己不会那么幸运,父母只是一般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家里哥哥姐姐一大堆,母亲为了让二姐接班,早早地就从毛纺厂退休了。大哥插队几年了,他在农村待得早就不耐烦了,一次次写信催父亲退休,只有父亲退休他才能从农村顺利地回到这座黑糊糊的城市里接父亲的班。大姐插队的时间最长,属于后来人们常说的...
作者:葛红兵希伐若的自我介绍我关心卡夫卡笔下的小人物。一个叫希伐若的人。可能很多读卡夫卡的人对这个人物都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真正的地是一个小人物。让我们看看他对待K的态度。起先他对K是彬彬有理的,甚至因为惊醒了他而向他表示歉意。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他主动地作了自我介绍,请注意,虽说是自我介绍,他却并没有真正地自我介绍,实际上他只是介绍了他的父亲是谁,他说自己是城守的儿子,而关于他自己的职位、姓名等等却不置一词,因而对于他是谁,我们其实还是一无所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真正的小人物,他是没有自我的,他对自己是那样地不自信,因而他在介绍自己时,总是通过介绍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来介绍自己,仿佛将自己同某个大人物联系起来,他自己才能获得足够的自我,才能在这个世界立足。...